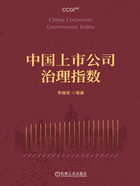
(三)高管治理
传统经济学观点认为,高管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作为股东财富的受托人,高管履行受托责任必须进行一定的激励约束安排。随着研究发展,学者关注视角开始从管理层整体向管理者个人转变,研究视角更加倾向高管行为背后的复杂行为特征及其经济后果。中国行政经济型治理模式下,国企高管行政人和经济人的双重身份,催生了“好处吃两头、空子钻两个”的独特高管治理风险。
高管特质方面,早期的研究文献相对较少,2006年之后,Fabrizio、van Liere和Pelto(2014)发现任期长的CEO为了个人业绩,倾向于用盈余管理来粉饰其过度投资的行为,从而助长了企业盈余管理现象的发生。在国内资本市场上,陈德球、雷光勇和肖童姝(2011)也证实了相关观点,即CEO任期促进盈余管理发生的概率,这在民营企业中尤为明显。但是,岑维和童娜琼(2015)指出了不同的观点,认为高管任期与盈余管理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直线关系,而是U形关系,并指出CEO和CFO(首席财务官)最好的任期分别是3年和5年。李晓玲、胡欢和程雁蓉(2015)发现由于女性CFO的谨慎性和风险偏好等的影响,女性CFO所在的上市公司真实盈余管理水平显著低于男性CFO所在的上市公司。但同样,相比于年轻的CFO,年长的CFO更加保守,注意对风险的规避,因此CFO年纪越大,其所在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也越低。类似地,CFO的学历水平和专业化程度也能抑制公司的盈余管理活动。董事会秘书在具备财会背景时,公司的盈余信息含量更高(姜付秀、石贝贝和马云飙,2016),降低了公司内外部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赵玉洁和崔玉倩(2019)则发现,高管的贫困经历导致其形成了风险规避的特征,所以降低了盈余操纵的概率。周冬华、黄雨秀和梁晓琴(2019)的研究发现,董事长们年轻时做知青上山下乡的经历,促使他们形成了风险规避的经营风格,降低了风险承担能力,提高了企业会计稳定性,即提高了会计信息质量。王元芳和徐业坤(2020)发现,有军队背景的高管与标准无保留意见存在正相关的关系,高管的军队生涯使其形成了正直自律和重视规则的价值观念,实施盈余管理行为的可能性小。
高管激励方面,早期文献直接关注高管激励对公司绩效的激励效用,产生了三种理论假说,即利益协同假说、管理层防御假说又称堑壕效应(Fama和Jensen,1983)、区间效应假说(McConnell和Servaes,1990)。Jensen和Meckling(2019)提出的利益协同假说,认为随着管理层持股比例增加,管理层目标与股东目标趋于一致,代理成本得到降低。他们认为代理成本是股东和管理层因为目标不一致所产生的效率损失。管理者不拥有企业股权,需要承担所有私人成本却只能获得部分利益。如果管理者增加在职消费,则可以获得全部利益,只承担部分成本。因此,随着管理者拥有的公司股份数量增加,管理者目标与股东目标趋于一致,代理成本得到控制。Aboody、Johnson和Kasznik(2010)研究股票期权激励再定价与公司业绩的关系,发现相对于未实施再定价的样本公司,再定价的样本公司业绩显著得到改善。虽然他们的研究支持线性关系,但是更多的文献认为高管激励与公司业绩存在非线性关系。Lian、Su和Gu(2011)的研究认为高管激励与公司业绩正相关。国内有关高管激励的研究也是遵循机会主义假设和有效契约假说的研究范式,检验利益协同假说、管理层防御假说以及区间效应假说。李增泉(2000)研究认为,管理层持股有助于企业业绩提升,支持利益协同假说。周仁俊、杨战兵和李礼(2010)的研究结论与此相同,并认为非国企的管理层持股与业绩之间的相关性更强。黄国良、董飞和李寒俏(2010)基于三次函数模型的检验结果,均支持两者之间“存在N形曲线关系”的结论,这表明当管理层持股比例较低或较高时,协同效应占主导地位,而当管理层持股比例在中等水平时,侵占效应发挥了主导作用。汤业国和徐向艺(2012)的研究支持区间效应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