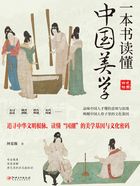
第四节 庄子:自由之美
庄子,名周,战国时期宋国人,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是老子之后道家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与老子并称“老庄”。他的思想比老子更具体、更形象,被闻一多评价为“最真实的诗人”。
“道”生万物是老子最先提出来的,庄子作为道家学派的后起之辈,也继承了这一思想。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庄子·知北游》)这里的“大美”就是道。庄子认为,对于“道”的观照就是人生最大的快乐。但与老子不同的是,庄子没有把“道”作为一种生天地万物的物质形态,而是将宇宙本源的这种物质形态以“气”去代替。他说:“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故万物一也。是其所美者为神奇,其所恶者为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气耳。’圣人故贵一。”(《庄子·知北游》)在庄子看来,人的诞生是由于气的聚合,气聚合到一起便形成了生命,气一旦离散,人便死亡。无论我们平时看到的美好的东西,还是腐臭的东西,其实质也不过是气而已,它们之间是可以相互转换的。我们平时所说的“化腐朽为神奇”就是这个意思。因此,天地万物实质都是气而已。庄子这种思想就是他哲学中的“齐物论”思想,万物同一,万物有这种物质上的统一性,可以相互转化,而不是固定不变的。这也是他思想中充满辩证性的特色所在。
庄子的美学思想是围绕着“自由”而展开的。这种“自由”来源于对“道”的观照,他通过孔子与老子的对话,说明了如何实现这种观照。有一次孔子去见老子,老子刚洗完头发,正披头散发等待它自然晾干。孔子看他的样子一动不动有如枯木一般,很是不解。老子回答说他在神游物之初的混沌之境。孔子问他如何能达到这种境界,老子举了几个例子,他说食草的动物不会因为沼泽地脏了要去更换而烦忧,水里的虫类不会因为水脏了要换水而烦恼,只是一些小的方面的变化,但基本的生存条件并没有失去,人心里就不会有喜怒哀乐的情绪。遗弃身上的附属之物就像遗弃泥土一样平常,如果能达到这样就可以进入观照“道”的境界了。在庄子看来,如果能排除生死得失祸福之类(这些都是凡人所日日忧虑的东西)的忧虑,也就是达到一种“无己”的境界,那就是得“道”了。庄子所说的“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逍遥游》),也是这种境界。他进一步将这种“无己”“无功”“无名”的状态归之为“心斋”,或者叫“坐忘”。“心斋”就是空虚的心境,只有心境空虚,排除杂念,才能把握世界“道”的本质;“坐忘”就是不再去考虑形体、五官等外在的生理机制的特点,从世人每天所争论的各种算计得失中解脱出来。达到这两种境界也就是达到了“无己”“丧我”的境界,这时才能“观道”,进入“至美至乐”的自由之境。也就是庄子在《逍遥游》中讲的“游”的境界:心外无物,无物无己,天地之间,任思想自由驰骋。
庄子提出的“心斋”“坐忘”境界是中国美学理论上的一大贡献。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一方面,从艺术欣赏的角度来看,如果审美者不能摆脱实用、功利等目的,就无法发现真正美的自然。《庄子·田子方》中有个著名的例子“解衣般礴”可以说明这一点。宋元君想要人为自己画画,众位画师都拜揖而立,恭恭敬敬地润笔调墨准备着。有一位后到的画师,不慌不忙悠闲自如地走着,受命拜揖后也不在那站着,而是往馆舍走去。宋元君派人去看,见他脱掉上衣赤着上身盘腿而坐。宋元君说:“可以了,这位就是真正的画师。”“解衣般礴”遂成经典,后世用这个词语形容艺术家创作时无拘无束、自由发挥的状态。另一方面,从艺术创造的角度来看,如果艺术家不能排除利害得失等私心杂念,就无法获得创造的自由和乐趣,也创造不出真正美的艺术品。《庄子·养生主》中也有一个大家熟知的例子,那就是“庖丁解牛”。庖丁之所以能不用眼睛看就可以游刃有余地将一头牛解剖完毕,是因为他已经有了三年的扎实的解剖经验了,他熟悉牛的每一个身体部位的构造和特点,因此才能运气凝神,手起刀落,解牛夺冠。也就是说,庖丁已经把握了“解牛”之“道”,他不用再去像刚开始解牛般战战兢兢考虑牛骨位置,牛脏在哪,也不用去想如果解不好会不会丢脸或者失去参赛资格……他能达到这种排除杂念的境界的原因,是他已掌握并熟谙了这里面的规律,于是他在这个过程中获得的只有解牛带来的自由和快乐,他到达了一种高度自由的境界,他的解牛过程也像美的艺术品一样获得了赞美。我们当代所推崇的“大国工匠”精神,有许多艺术家就是因技艺的娴熟高超,在艺术创作中达到了高度自由的境界,也就是美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