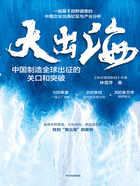
小商社填充空白
日本企业在海外拓展业务的时候,大小商社的身影都活跃其中。即使是中小体量的商社也摆脱了“低进高出”的贸易形态,成为“贸易与工程”的结合体。
尽管三菱商事、三井物产这种巨无霸商社令人印象深刻,但很多日本制造企业实际依赖的是日本中小商社。这是一支活跃的轻骑兵。
日本山善商社(YAMAZEN)就是其中之一。山善商社主要提供机床、工具零部件等服务,在中国、越南、墨西哥等地提供广泛的工具解决方案。2024年预计年收入约240亿元,但归母净利润率却只有0.5%。虽然看上去盈利能力比较弱,但它却是强大的日本制造生态的关键部分。
山善商社一共有员工2 700人,其中海外有1 200人。在中国有400人,在墨西哥有50人的团队。山善在海外有66个办事处,已经超过了国内的53个。其中,在墨西哥重要工业城市如瓜达拉哈拉、蒙特雷、克雷塔罗等都有办事处。许多海外办事处也有展厅和仓库,建立了备件支持中心。山善商社是一个小型的超级工厂综合体,它将国内3 000家制造商和全球5 000家分销商的渠道整合在一起。它为当地的日本零部件企业提供的是一套“全工厂解决方案”,将各家制造商与分销商的备货,整合成一种能力界面,提供给日本厂商。它的海外人员中,有1/4的员工是拥有复杂技能的工程师。山善没有工厂,它通过供应链服务的方式,嵌入日本海外企业之中。
这种现象非常普遍。日本电计株式会社(Denkei)专注于电子测量仪器,每年销售额大约50亿元。企业有千人规模,一半是海外雇员。与山善类似,海外分支众多,跟国内的数量相当。这家公司与5 000多家制造商合作,相当于每家平均销售额只有100万元。它可以向用户提供数万种产品,从而覆盖每个细分领域。这种密集覆盖,可以让用户完成一站式采购。这类企业不只卖产品,备件与维修服务也是必不可少的。它也会建立服务中心,购买测试设备,向中小用户提供类似振动、电性能的测试服务。大量类似日本电计这样的小型商社,在中国、越南、北美等国家和地区建立起广泛的网络,与日本企业交织在一起。
这些商社是日本海外工厂与日本国内工厂的交会点。日本国内名不见经传的小制造商,通过各种商社进入全球制造业的脉络之中。如果说德国“隐形冠军”企业独自闯荡天下,那么日本大量的微型企业则是通过商社渠道进入了全球的价值链体系。日本商社企业有三个共性,那就是“对半机构、对半雇员和对半工贸”:海外机构数量与国内办事处基本相等,海外雇员与国内员工大致各占50%,而贸易与服务的业务也大致各占一半。
日本企业的海外空间的拓展,体现了一个集团军的行动规则。供应链上的链主企业会带动一级供应商一起建立工厂。与此同时,日本的大商社、小商社也会同步跟进。在海外落地工厂的企业,往往并不会向设备、材料、部件的供应商直接进行采购。这种工作广泛依赖商社来推动。
日本企业广泛地使用商社这种桥梁,尤其在墨西哥这样的“供应链荒野”。在莱昂州有一家日本汽车零部件厂家,它是丰田汽车的二级供应商。它的大部分供应链就是由几家日本商社来完成的。
即使工厂设备进行小规模的改造和机器移动,也不是通过设备厂商来实现的,而是由日本商社代劳。不同的商社会有不同的分工和不同的业务范围。一个企业往往只需要几家商社提供服务,就能基本解决大部分车间的生产供应。只有个别大型设备,才会由企业跟供应商直接完成供货对接。
日本商社具有深度的工厂基因,注重车间现场的工程服务能力。不妨说,很多日本商社,其本质是披着商贸外衣的工程服务公司。它们能够提供多品牌产品的集成服务。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日本商社的零部件相对比较贵,日本企业也能接受。高出来的价格,其实是服务能力的溢价。有了商社的支持,日本工厂就不需要到外部去寻找供应链资源,而可以将精力集中在提高工厂的效能上。
如果下游企业是大齿轮,供应商是小齿轮,那么二者之间的咬合,要依靠强力的润滑油膜。这一层正是日本商社的作用。由于采用轻资产,更注重工程技术的整合,日本商社成为商务连接与知识能力嫁接的典范。
从日本制造的风格来看,日本企业具有一种“商社偏好”的销售文化。日本产品提供商习惯跟商社配合,将商社销售作为公司对外发展战略的一部分。双方共同绑定的契约精神非常强烈,而在价格控制方面也很有默契。商社的定价不会过高也不会过低,严格遵守制造商的定价原则。
在日本企业的生态体系中,商社是一个长期存在的中间层。下游的制造商会为商社留出利润,而上游的供应商也对商社比较友善。整个供应链都在有意识地保护“供应商—商社—工厂”这样“一轨半”的夹层商业结构。这是日本海外制造形态的特征。人们不仅要看到日本商社的形态,还要理解其背后的商社文化。
中国企业出海目前很少采用这种第三方服务的商社模式。中国大型企业出海建立工厂时,往往通过总部采购国内产品,直接运到当地。同时对于小件商品也会通过日本商社进行采购,后者对于多元化的产品有着很强的服务能力。在中国制造体系中,能提供专业化工程服务的类似商社组织尚未形成独立的形态。企业没有将中间利润留给商社,部分原因是后者还没有提供重要的价值。这也意味着中国制造能力还没有完成专业化分工。以知识能力为基础的工程服务层依然有所缺失。当中国制造开始进入全球化进程中,供应链的复杂度大幅度提高,贸易、工程与物流相结合的中间服务层的价值显得日益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