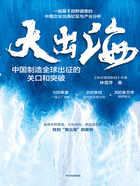
大商社成为护卫舰
日本企业集体出海,得益于它拥有保驾护航的商业系统。这既有日本商社这样独特的“产业组织者”,也有国家级的海外投资促进系统。
商社支撑了半个日本工商业帝国。“商社”的名字听上去是一个贸易公司,但它早已超越中介的功能。
日本商社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治维新时期。它是为了夺回外国商社的统治性贸易权而设置的,因此天然具有政商一体的财阀性质。在漫长的历史中,商社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无疑,这是行之有效的海外行走城堡,而商权的确立则是关键要点。
企业选择出海,位置非常重要。日本商社从全球版图出发,形成了不同的布局。欧美是日本高端产品的消费国。东南亚市场潜力大,是日本中低端产品的出口国,以及在地生产的基地。希腊是连接欧洲与亚洲的枢纽,作为日本钢铁加工出口基地,从空间上形成旋转门效应。
日本商社的海外机构会跟日本企业的发展同频共振。商社布局流通渠道的时候,会与制造业在地理空间上紧密呼应。1984年,当日新制钢、日本钢管、川崎制铁三大钢铁生产企业在美国大举投资的时候,三井物产商社也积极建立钢铁销售公司,向流通渠道渗透。[1]这种扩展不仅限于销售,三井物产还投资钢铁加工设施,以确保日本钢铁在美国能够拥有一个前后相通的供应与分销管道。
制造业企业的国际化需要商社的流通渠道出海相陪。日本汽车、电子产品开始在全球流行的时候,离不开商社所搭建的健康网络。1985年三井物产为了促进富士重工的汽车销售,投资收购欧洲一家大型汽车的销售公司,组织汽车在欧洲当地销售。
可以说,生产资本与商社资本形成牢不可破的联盟。三菱商事与三菱汽车、丸红商事与日产汽车、伊藤忠商事与马自达、三井物产与富士重工等,都在早期通过合资建立了销售公司。
日本“综合商社”的含义,已经从“多样类综合性的商品”转化为“综合性的功能”。它通过投资产业,将业务版图扩大到供应链的上下游。
日本商社是一个有着神经末梢的商业有机体。规模的扩张并没有减弱它对社会变化的敏感性。得益于它有多种商业形态的布局,才能让大象拥有蜜蜂一样的感知力。商社具备整合全球价值链上下游的能力,然而这种能力却隐藏在幕后。台前那些耀眼夺目的品牌商,遮掩了商社作为产业组织者的不易察觉的布局。
优衣库从1998年开始走向自建营销渠道之后,很快与西班牙ZARA、瑞典H&M和美国GAP一样,成为全球化快服装公司的轻骑兵。GAP因行动缓慢而逐渐失去先锋位置,前三者则依然越战越勇。优衣库在2024年的收入达到了破纪录的1 500亿元。
然而优衣库并非一个企业在战斗。三菱商事有一支庞大的队伍,其纱线、印染、面料、生产都有全方位的支撑服务。优衣库的成功,固然有柳井正高超的管理能力,但从幕后英雄来看,三菱商事是最大的功臣。
可惜大家似乎都在遮掩这种光芒。《优衣库:经济衰退期的二十年增长奇迹》一书,把优衣库描述成一个没有弱项的公司。书中只简单提到了总经理来自三菱商事,其他则一笔带过。这种叙事方式对三菱商事并不公平,也容易让人忽视日本商业系统的整体性。
三菱商事具有很强的前后贯通能力,能够将时尚信息与生产能力进行嫁接。它有一个时装总部位于东京,也会参与品牌商的商品企划。而在上海和香港地区都有时尚基地,并在青岛和宁波设置分支机构,负责管理在中国的服装生产。商社与快时尚服装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深度合作,表明日本企业的出海往往是通过系统制胜的。
日本企业普遍具有一种商业互助性,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日本钢铁厂刚开始发展的时候资金很少,只能集中精力更新高炉设备状态。而对于原料的低成本采购,则交由商社来完成。商社也会积极地去构建新的业务体系。例如,开始向矿山融资以获得优质炼焦煤,或者自行投资去建设矿山,等等。这些使商社成为钢铁行业价值链上的一个关键环节。
在日本企业国际化的早期,商社已经开始采取这种联合出海的策略。日本商社与企业构建了一种独特的合作关系。除了股份,还有人力资源的相互嵌入。相互派遣干部是一种传统。三菱商事会向三菱化工、三菱制钢、三菱汽车等企业派遣管理人员,而三菱电机、三菱重工等骨干企业也会向三菱商事派出监事官。[2]
这种人事安排,不仅强化了企业之间的人情联络,也大大加强了双方的业务搅拌。人事上的深度连接,使得价值链具有通透合一的力量。在很多时候,日本商社也会直接参与经营。
1998年,伊藤忠商事取得了日本“全家”超市的部分股权,此后陆续追加投资。2018年,伊藤忠把出资比例提高至50.1%,使其成为子公司。而在2020年,则投入50亿美元实现全资持股。商社拥有零售商的布局,在日本并不少见。2002年,三菱商事投入13亿美元收购了罗森便利店33%的股权,后来在2016年将持股比例提升到一半。最初这个决定源自三菱商事在2001年的战略转变,它出乎意料地成立了零食消费部门。这样就可以打通粮油原料、中间品的上游大宗商品与下游零售之间的通道。如果无法有效了解下游零售渠道,处于上游的决策就总是带有一定的模糊性。而唯一的方法,就是让下游跟上游一样透明。2023年,全家超市和罗森便利店的营业额分别是200亿美元和180亿美元,这两家零售超市已经成为各自母商社现金流的重要流入者。
然而,商社从来不是甩手掌柜。三菱商事派出了管理人员,进驻罗森的业务现场。这并非出于管理的需要,而是来自对一线消费者趋势的渴望。双手沾泥,在一线感知消费端的变化,这是日本商社的一个显著特征。
三菱商事在泰国的布局也不同寻常。泰国是皮卡大国,而日本则采用了生产制造与流通渠道双管齐下的策略。日本五十铃与泰国本地商业集团三宝,形成合资公司,生产五十铃商用卡车。五十铃负责生产制造和技术,而三菱商事则几乎包揽了零部件、销售、售后服务、金融信贷等全部价值链环节,其中也包括全球汽车的布局。2023年五十铃汽车在泰国的产量为30万辆,本地销售新车12万辆,市场占有率达到44%,其余则面向出口。无论是本地还是出口,三菱商事都起到了巨大的协同作用。这也是日本企业利用系统性合力开拓海外市场的又一成功案例。
在这个过程中,日本大企业也会自行组织产品进出口和供应链编排,似乎呈现出日本企业出海的“脱综合商社”现象。然而,依然没有一家生产企业能够打通全部关节。在经济波动、政局困难的时候,大企业往往依然会借助商社的力量来摆脱经济扰动。商社资本只要加强自己的能力,往往使得生产资本和制造商都很难抵御合作的诱惑。
“脱综合商社”从未实现。在日本企业汹涌的大出海过程中,商社这个古董级的商业形态依然保持活力。在2004年到2014年的10年中,三菱商事、三井物产、住友商事、伊藤忠商事和丸红这五大综合商社,累计纯利润排名均能进入日本企业前20。2023年,在地缘政治更加动荡、信息瞬息多变的供应链大分流之际,三井物产净利润达到460亿元,日本本田为600亿元,它们都是顶流的超级利润机器。三菱商事只比三井物产略低,而在商社中排名第三的伊藤忠商事,利润也达到了400亿元。
日本商社经历了多次“商社无用论”,但即使在日本企业巨头越来越强大而独立的时代,商社依然保持着惊人的商业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