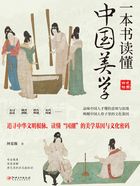
第一节 《淮南子》:美与美感
到了汉代,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的思想局面已经趋于综合。如果说从孔孟之道及至《荀子》,再到《吕氏春秋》表明了儒家思想的综合趋势,那么《淮南子》就是老庄之后道家思想的延续与综合。汉初面对秦末战乱的破败景象,统治者采取“与民休息”的黄老之学治世理政,《淮南子》就是产生于这样的背景下。
《淮南子》由西汉淮南王刘安组织其门客集体编著。刘安是汉高祖刘邦的孙子,寿春(今安徽寿县)人,西汉思想家、文学家。他好读书,善文辞,礼贤下士,宾客盈门。《淮南子》原名《淮南鸿烈》,它以道家思想为主,兼容儒、墨、道、法等多家思想,内容庞杂,其中涉及的美学思想虽然零散,但对后世有很深的启发。
关于生命问题,一直是先秦以来美学所关注的重点之一。比如《周易》提出的与“象”相对应的“形”,《庄子》中提到的形神问题,《淮南子》在前代的基础上,把“形”“气”“神”三个概念放到一起进行谈论:“夫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则三者伤矣,是故圣人使人各处其位,守其职而不得相干也。故夫形者,非其所安也而处之,则废;气不当其所充而用之,则泄;神非其所宜而行之,则昧。”(《淮南子·原道训》)《淮南子》认为,“形”是人的身体寄托的物质外壳,“气”是充满于身体各处的一种生命物质,“神”就是人的精神,是统率整个身体的关键所在。这三者是一个相互统一的整体,缺一不可。有时,《淮南子》会在“形”“气”“神”这三者之外,再加上一个“志”,构成生命的“形气神志”模式。这里的“志”有意志、理性思维的意思,这样在原来道家思想“神气”说的基础上,其实多了一层儒家思想的烙印,体现了儒家严格约束自身和入世治世的思想。
对于美丑,《淮南子》首先肯定了它的客观性。如美玉即使掉到淤泥中,廉洁的人也不会放弃它。破瓦罐、烂席子即使被摆在华美的地毯上,贪婪的人也不会去拿取。这说明美与丑本身是客观存在的,人们并不能随心所欲地加以改变。虽然美丑是客观的,但也不是绝对的,再美的事物也有丑的地方,再丑的事物也有美丽之处。外形粗糙的石头在一般人眼中是丑陋的,但在赏石家眼中,却可能因为它的独特外形而具有特别的观赏价值,从而价值倍增。在西方人眼中优雅的东方美人,在中国人眼中可能因为五官不符合一般审美而否定她的美。“夫夏后氏之璜,不能无考,明月之珠,不能无颣,然而天下宝之者何也,其小恶不足妨大美也。”(《淮南子·汜论训》)一块天然的玉石,你仔细看,里面不可能没有一点瑕疵,有的包含一些杂质,有的在上万年的石化过程中还可能有其他矿物元素沁过的痕迹,然而这些小的“丑”并不妨碍它的大“美”。在《淮南子》看来,美丑的判定要通过一个整体去看待,而不能只看局部。我们说的“人无完人”也是这个道理,再厉害的治国君王也有他治理不善的地方。再罪大恶极的人,性格中也会有一两处闪光点。从这点上讲,《淮南子》充满了辩证法思想。
在美的存在形式上,《淮南子》认为美的形式多种多样,而非唯一。就像我们在举行选美比赛的时候,每个国家和民族都会有自己的审美标准一样。先秦时期诸侯争霸,每个国家的治理方式不同,它的音乐也不尽相同。孔子认为《韶乐》尽善又尽美,《武乐》只有美而没有善,但其他人未必这样认为。这种多样化的发展模式,对艺术是有积极意义的。
人们对美之所以会产生不同的认识,有时候甚至是截然相反的感受,《淮南子》给出了一个重要解释,那就是美感的差异性。“夫载哀者闻歌声而泣,载乐者见哭者而笑。哀可乐者,笑可哀者,载使然也。”(《淮南子·齐俗训》)“心有忧者,……琴瑟鸣竽弗能乐也。”(《淮南子·诠言训》)一个心里忧伤的人,听到一首舒缓优雅的轻音乐也会落泪,一个满心欢喜的人即便见到哭泣的人,也不一定会跟着他一起哭。审美感受的不同,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欣赏者本身心理状态的原因,也与他的审美鉴赏力水平有关。《淮南子》还提到了审美感官的问题,认为虽然穿衣吃饭是人们维持生命的基本条件,但如果生命仅限于此,是感受不到美的。这里面提到了两个重要的器官——耳、目(中国古人认为,听觉与视觉是与人的审美直接相关的,因此耳、目在审美上比其他五官要重要得多)。但是光有耳、目还不够,还要依靠“形气神志”这些心理系统,才能真正感受到美。《淮南子》中的这些论述对于后世的艺术接受问题提供了许多启发。
另外,《淮南子》关于美学思想还有很难得的一点,就是它提到了劳动的作用:“清醠之美,始于耒耜,黼黻之美,在于杼轴。”(《淮南子·说林训》)在这里,“醠”指美酒,“耒耜”是古代的一种劳作农具。也就是说,人们之所以能品尝到酒的美味,是因为人们辛勤劳动种植了庄稼,继而用劳动的果实酿造了美酒。它将美与人的社会劳动联系起来,这比马克思、恩格斯的“艺术劳动说”早了近两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