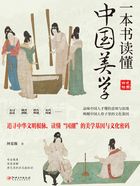
第七节 《周易》:“象”之美
《周易》是一部古老的哲学著作,分为《易经》和《易传》,作者暂无定论。《易经》的内容是用来卜筮的卦和卦辞;《易传》是对《易经》的解释和在此基础上的发展,它保留了《易经》中的巫术宗教形式,借此搭建了一个以阴阳为核心的哲学思想体系,充满了深刻的辩证法思想。《周易》自汉代起就成为儒家经典,是群经之首,它虽然没有直接谈到美学,但是它的哲学思想为中国古典美学奠定了基础,尤其是用“象”来表示万事万物,是意象理论的来源。
《周易》源自上古时期的占卜,跟我们现在所说的“算命”类似。那时候人类的生产能力和认识自然的能力有限,把一些未知的事物和现象都归结为神灵的作用,需要借助神灵之力去占卜未知,以增加行事成功的概率。《易经》中最基本的就是“八卦”——乾、坤、震、巽、坎、离、艮、兑。这是远古先民从日月星辰、四季轮回中强烈感受到规律的存在,并以天、地、雷、风、水、火、山、泽等不同的品性,对自然进行认知。他们从占卜材料中构建了一套模式,叠加而成的八卦对应着各种祸福,用自然的形象来象征。因此,它又是中国古代一套有象征意义的符号体系。每一卦形都有一个基本的意指,如以乾卦的“天”意指“健”,以坤卦的“地”表示“顺”,以震卦之惊“雷”意指动,以巽卦之“风”表示“入”,以坎卦之“水”谓之“陷”,以离卦之“火”意指“离”,以艮卦之“山”意指“止”,以兑卦之“泽”谓之“说”。在“八卦”基础上又延伸出了“六十四卦”,这样一来就几乎把大千世界的各种状态都包罗进去了。可见这套以自然万物象征世间形态的符号体系,其形成离不开“象”(形象)的基础。
《周易》中最重要的美学贡献就是提出了“象”的命题:“《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易传·系辞传》)整部《易经》都是“象”,都是以形象来表明义理。艺术形象以形象来表达情意,《易经》以形象来表达义理,二者虽然貌似不太一样,但在借形象来表达社会生活的内容方面,却是相通的。比如《周易》中“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中孚·九二》),意思是两只白鹤在树荫里唱得多好听呀,让咱们一起来快乐地干一杯吧!这与《诗经》中的“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诗经·小雅·鹿鸣》)何其相似,二者运用的都是我们所说的“赋、比、兴”中的“兴”的手法,即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从这点上讲,《易经》虽然不是直接的审美形象,却可以通向审美形象。
《周易》不仅提供用符号来象征实物的方法,强调了“象”,而且还提出了“立象以尽意”和“观物取象”的命题。
先看“立象以尽意”。《周易》通过“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来引出“立象以尽意”的命题。也就是说无论书信(文字)还是语言,都无法完全准确地表达出个人的思想内容,那怎么办呢?只能通过“立象”的方法来达到准确表达个人思想内容,通过采用形象的办法来达到文字和语言无法表达的含义。这就是形象的高明之处。因为语言和文字是经过抽象化了的、概念化了的东西,是将个别的东西进行普遍化归纳的结果,那再用它去表达个别的想法和思想,肯定会存在“言不尽意”的结果。而通过“立象”的方法为什么能化解这一矛盾呢?因为形象是个别的东西,它是生动、感性的实体对应物,通过它可以以小喻大、由此及彼,就像艺术形象以个别表现一般,以有限表现无限的特点一样。可以说,“立象以尽意”为我们美学中常说的艺术典型的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
再来看“观物取象”。《周易》中讲:“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易经·系辞传下》)古代伏羲氏治理天下的时候,抬头看天象,低头观地法,从鸟兽纹理以及大地景观中总结规律,近处择取众多自己亲身体验的事物,远处择取众多观察到的事物,于是根据这些情况开始创作八卦,用来传告治国良才的仁慈政治措施,用来类推宇宙间一切事物的实际情况。这是告诉我们圣人是怎样从自然和生活现象中总结规律,创造出“象”来的。这个过程也说明“象”表现的不仅仅是事物外在的形态特征,更包含着内在的变化规律。比如《易经》中的乾卦,象征着天,意指“健”。《周易》把“天”作为首项命题推出,意味着整体格局的宏大、开阔、刚健。正是“天”包容了春、夏、秋、冬,运行不息,变化无穷,构建起世间的勃勃生气。《周易》以此开局,格局高畅,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初醒之气。可见“观物取象”不仅表明了古人如何从自然生活现象中总结规律的过程,也体现了古人“仰观俯察”的一种整体观的观物方式。王羲之《兰亭集序》中的“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这告诉我们,观察事物不能只着眼于局部或者某一孤立对象或者某一个固定的角度,而要着眼于宇宙万物,着眼于整体。艺术也是如此,只有仰观俯察,游目骋怀,才能得到审美的愉悦。
除了“象”的命题,《周易》中还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如“阴”与“阳”、“刚”与“柔”等,这些对立统一的概念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古典美学的思想文库。我们看《周易》中八卦以及由它重叠而成的六十四卦,最初就是由阴阳二爻构成的。“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易传·系辞上》)古人仰观、俯察取类比象,将自然界中各种既对立又相互联系的现象,如天地、日月、昼夜、寒暑、男女、上下等抽象归纳出“阴阳”的概念,把矛盾运动中的万事万物概括为“阴”“阳”两个对立的范畴,并以双方变化的原理来说明物质世界的运动变化。即便生活在当代的我们,生活中也处处充满阴阳的智慧,如自然界中生物的基因、人工智能中的二进制都充分彰显了阴阳的生命力。美学上关于“气”的讨论,后来谢赫“气韵生动”的观点,也都是建立在以“阴”“阳”为代表的辩证法思想的基础上。
《周易》为中国古典美学的“象”的概念奠定了基础,蕴含着丰富无比的辩证法思想,是中国古典美学不可或缺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