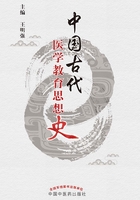
第三节 古代医学教育人才论
教育是培养人的工程,培养什么样的人决定了教育对象的选择、教学内容的设置和考核机制的确立。“人才观”是教育的核心问题,决定了教育的目标和整体走向。
一、古代医学教育的人才标准
(一)医德为先
中国古代历来强调德才兼备,以德为首。医学领域亦然。吴瑭在《医医病书·医德论》中论述才与德的关系云:“天下万事,莫不成于才,莫不统于德。无才固不足以成德,无德以统才,则才为跋扈之才,实足以败,断无可成。有德者必有不忍人之心。不忍人之心油然而出,必力学诚求其所谓才者。医也,儒也,德为尚矣。”习医者首先要做德行高尚的人,历来名医多为典范,如朱丹溪“简悫贞良,刚严介特,执心以正,立身以诚,而孝友之行,实本乎天质”(《丹溪翁传》)。德的含义颇广,就医而言,概而论之,其要有五。
1.尊重生命、生命至上的理念
习医者要将生命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否则,不可为医。张景岳在《景岳全书·误谬论》中言:“矧医之为道,性命判于呼吸,祸福决自指端,此于人生关系,较之他事为尤切也。以此重任,使不有此见此识,诚不可猜摸尝试以误生灵。矧立法垂训,尤难苟且,倘一言失当,则遗祸无穷,一剂妄投,则害人不浅。此误谬之不容不正也。”其在《类经图翼·自序》中云:“夫生者,天地之大德也。医者,赞天地之生者也。人参两间,惟生而已,生而不有,他何计焉?”
2.慈悲仁爱之心
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云:“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这种大慈恻隐之心是糅合了儒佛两家思想而达至的普济世人的高尚境界。
3.乐道有恒之志
医术精微,非深好此道并持之以恒者难成大器。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云:“医方卜筮,艺能之难精者也,既非神授,何以得其幽微?世有愚者,读方三年,便谓天下无病可治;及治病三年,乃知天下无方可用。故学者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深自误哉!”历代名家无不痴迷医道、精勤不倦,朱丹溪慕名向罗知悌求教,“凡数往返,不与接。已而求见愈笃,罗乃进之”(《丹溪翁传》),正是凭着虔敬之意、不懈之志才得以受其所教。赵学敏在《串雅·序》中叙述自己自幼痴迷医术,老而靡倦。曰:“予幼嗜岐黄家言,读书自《灵》《素》《难经》而下,旁及《道藏》《石室》;考穴自《铜人内景图》而下,更及《太素》《奇经》;《伤寒》则仲景之外,遍及《金鞞》《木索》;本草则《纲目》之外,远及《海录》《丹房》。有得,辄钞撮忘倦,不自知结习至此,老而靡倦。”
4.谨严审慎之风
医关乎人命,不可不慎,急躁粗率之士不可为医,自满炫耀之士不可为医。孙思邈告诫云:“夫大医之体,欲得澄神内视,望之俨然,宽裕汪汪,不皎不昧。省病诊疾,至意深心,详察形候,纤毫勿失,处判针药,无得参差。虽曰病宜速救,要须临事不惑,唯当审谛覃思,不得于性命之上,率尔自逞俊快,邀射名誉,甚不仁矣!夫为医之法,不得多语调笑,谈谑喧哗,道说是非,议论人物,炫耀声名,訾毁诸医,自矜己德,偶然治瘥一病,则昂头戴面,而有自许之貌,谓天下无双,此医人之膏肓也。”(《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
5.传道授业之责
医道传承乃千秋伟业,是每一位医家不可推卸的责任。仅成就自身而不传承或传非其人,不能称为有德之医。《素问·气交变大论》中云:“得其人不教,是谓失道;传非其人,慢泄天宝。”王冰之所以历时十二载整理校注《素问》,正是出于“冀乎究尾明首,寻注会经,开发童蒙,宣扬至理而已”(《黄帝内经素问注·序》)。李杲为传授医道,自己供给弟子罗天益衣食起居,令其潜心医术,“临终,平日所著书检勘卷帙,以类相从,列于几前,嘱谦父曰:‘此书付汝,非为李明之、罗谦父,盖为天下后世,慎勿湮没,推而行之。’”(《医史·东垣老人传 》)
(二)精于“道”“术”
“呜呼!生民何辜,不死于病而死于医,是有医不若无医也,学医不精,不若不学医也。”(吴瑭《温病条辨·自序》)吴瑭此论可谓振聋发聩,让人警醒。学医之人倘无精心医术之志就不要学医,培养医学人才倘不能培养出医学精英就是失败的教育。中国古代自古就将医学教育看作精英教育,在学生选拔上“非其人不教”,在教学内容上穷究经典,在考核机制上极为严格。
所谓精,就要精医道和医术。“道”“术”贯通方为良医、上工。一个合格的医生首先要精通医道,医学教育偏于术而轻于道是无法培养出医学精英的。“道”是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最核心、最本原性的概念。“道”生化万物,为万物之母,同时又是万物运行最本原的动力。万物从“道”而来,依“道”而行,归“道”而去。医学是生命哲学,“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同样也是医学的精髓,人依循“道”诞生、生存、归去。如果违背“道”,灾祸就会降临。医学必本于道的理念在中国古代医学中可谓根深蒂固。“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道者,圣人行之,愚者佩之”(《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历代名医无不精于医道,扁鹊医术高明众人皆知,这种高明是建立在其医道精深的基础上,《史记》载其给虢太子诊病,未见其人而言病之所在,“越人之为方也,不待切脉、望色、听声、写形,言病之所在。闻病之阳,论得其阴;闻病之阴,论得其阳”,就是他精通医道的写照。
出于“天人合一”的理念,人与外在宇宙是浑融贯通的,对于人生命的把握,就不能局限于人体,而必须具有广博的知识。“《上经》曰: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素问·气交变大论》),“治不本四时,不知日月,不审逆从,病形已成,乃欲微针治其外,汤液治其内,粗工兇兇,以为可攻,故病未已,新病复起”(《素问·移精变气论》),“上而天时,五运六气之错综,三元更递之变幻;中而人事,得失好恶之难齐;下而万物,百谷草木金石鸟兽水火之异宜。非真用格致之功者,能知其性味之真邪?”(吴瑭《医医病书·医非上智不能论》)正是基于“天人合一”的理念,中国古代医学开创了世界上最早的天文气象医学——五运六气学说。五运六气的总思想是天气决定地气,天地合气又决定人的健康和疾病特征。其认为,天文、地理、气象、节候等自然生态环境变化有一定的规律,会影响人体生命,造成疾病,应该认识和利用这些规律预防和治疗疾病。
再者,一个合格的医生必须医术高超,仅仅坐而论道却无法为病人施治亦非良医。古代许多名医皆精通各术,如华佗方药、针灸、外科手术皆精。
(三)灵悟的思维能力
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强调习医者必须思维精微,“唯用心精微者,始可与言于兹矣。今以至精至微之事,求之于至粗至浅之思,岂不殆哉?”与西方主客对立型和直线发展型思维不同,中国古代思维方式基于“天人合一”的文化根基,注重整体及其关系,强调悟性与灵性,体现出充满智慧的圆融特性。就医而言,概举三项论之。
1.“致中和”的思维
在中国古代,几乎所有的哲学家都把“中和”看作事物内在最好也是最理想的状态。“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天地之气,莫大于和。和者,阴阳调”(《淮南子·氾论训》)。中,即不偏不倚,无太过、无不及的平衡状态;和,是对一切有内在联系的事物进行协调,使之达到和谐状态。“致中和”成为中国古代哲学中重要的思维方式。这种平衡与和谐的“中和”思想贯穿在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各个方面。如阴阳学说认为,在正常情况下,人体的阴阳相对平衡协调意味着健康,所谓“阴阳匀平,以充其形,九候若一,命曰平人”(《素问·调经论》),“阴平阳秘,精神乃治”(《素问·生气通天论》)。若体内阴阳的相对平衡被打破,出现阴阳的平衡失调,则人体由生理状态转为病理状态。针对疾病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阴阳平衡失调,治疗的原则是“损其有余,补其不足”,即所谓“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素问·至真要大论》),纠正失“中和”的无序状态,使其达到“中和”有序。中医学理论中的整体观、阴阳五行学说、辨证论治思想、生命观、发病观、对病和证的治疗等,无不是围绕着 “中和”思想展开的。“中和”思想虽源于哲学,但已与中医学融为一体,成为中医学的核心和灵魂。这种思想之所以能贯穿于中医学的始终,主要不是外在影响,而是中医学内在本质的必然选择。中医学的实践证实,“中和”思想不仅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建构起到重要作用,而且对指导养生防病、诊疗用药都有重要指导意义。
2.藏象思维
藏象思维是中国独特的以简御繁、以表知里、以类相通的思维方式。概而论之,其要有三。
(1)取象 《周易·系辞下》云:“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所描述的就是取象。中国的汉字可以说是取象思维的典型代表,尤其是象形字。这种取象思维有两个特性:形象性(直观)、符号性(高度归纳与以简御繁)。取象的目的并非仅是创制一些符号,而是要“类万物之情”,外在之象和内在之里是一种具有本质联系的对应关系。
(2)以象测藏 基于外在之象与内在之里具有本质对应关系的认识,“有诸内必形诸外”,反之,有诸外则必应于内。因此,对于无法直观认识的事物内在即可通过观察外在之象去揣测,亦即以表知里、以外测内。依据此种思维,中医形成了藏象学说。所谓“藏”,即藏于体内的脏腑;所谓“象”,即表现于外在的生理、病理现象。《类经》中说:“象,形象也。藏居于内,形见于外,故曰藏象。”在中医理论体系中,藏象学说是其核心,它对于阐明人体的生命活动、病理变化,以及指导临床的诊疗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3)以象比类 以象测藏仅是事物本身内外相联系的思维方式,对于事物之间互相联系的思维方式则是以象比类,亦称“援物比类”或“取象比类”法。此种思维方式认为象之相类,质必相通。这种思维的极致是道家的“道通为一”。《庄子·知北游》中东郭子问庄子“所谓道,恶乎在?”庄子答曰“无所不在”,甚至在“蝼蚁”“稊稗”“瓦甓”“屎溺”,其意即强调“道”之贯通万物,万物之间因“道”而相通相融。正是基于这种思维,哲学上的阴阳五行学说成为中医学的理论根基,人体之运行与自然界之运行无论在外相还是内在本质上都是相通达的。釜底抽薪法、增水行舟法、提壶揭盖法、导龙入海法等中医治疗方法则是此种思维方式的具体应用。
3.悟性思维
中医不是不需要分析、归纳、推理等逻辑思维,而是要在此基础上实现超越,达到悟性思维。逻辑思维是中医思维的浅层次,悟性思维方是中医思维的高层次。“医者,意也”的命题虽众说纷纭,但其核心指向是悟性思维却是无疑的。孙思邈在《千金翼方·序》中云:“若夫医道之为言,实惟意也。固以神存心手之际,意析毫芒之里。当其情之所得,口不能言;数之所在,言不能喻。”李治运序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亦言:“夫医者意也,方者法也,神明其意于法之中,则存乎其人也。父子不相授受,师弟不能使巧也。”这种思维方式是一种调动整个身心、极具个性化的对世界深层次的把握和领悟。《庄子·天道》中云:“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庄子·秋水》也说:“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所以轮扁的斫轮之术“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古代哲学家明示我们:第一,抽象的名言不能把握具体的事物。第二,静止的概念无法表达变化。第三,有限的概念不能表达无限。因此,只有悟性思维方能真正实现对世界的整体把握。所以,古代医家最具价值的成果之一就是医案,虽无过多理论阐述,却闪耀着悟性的光辉。章太炎曾言:“中医之成绩,医案最著,学者欲求前人之经验心得,医案最有线索可寻,循此钻研,事半功倍[2]。”悟性思维是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因此,中医学教育以耳提面命、随师学艺的传统方式为最有效亦是真正能够学到中医精髓的有效途径。
二、古代医学教育对象的选拔
目前中医药院校招生以高考分数画线为准则,这种唯分数的选拔标准对于医学教育是很不够的。这与古代对医学教育对象选拔的极其重视形成鲜明对比。
《灵枢·官能》中云:“得其人乃传,非其人勿言。”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序》中云:“夫天布五行,以运万类,人禀五常,以有五脏,经络府俞,阴阳会通,玄冥幽微,变化难极,自非才高识妙,岂能探其理致哉?”孙思邈《大医精诚》中言:“唯用心精微者,始可与言于兹矣。”徐大椿《医贯砭》中言:“盖医者,人命所关,固至难极重之事,原不可令下愚之人为之也。”晋·杨泉《物理论》云:“夫医者,非仁爱不可托也,非聪明理达不可任也,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徐大椿更撰有《医非人人可学论》以警世人。
今之学医者,皆无聊之甚,习此业以为衣食之计耳。孰知医之为道,乃古圣人所以泄天地之秘,夺造化之权,以救人之死。其理精妙入神,非聪明敏哲之人不可学也。黄帝、神农、越人、仲景之书,文词古奥,搜罗广远,非渊博通达之人不可学也。凡病之情,传变在于顷刻,真伪一时难辨,一或执滞,生死立判,非虚怀灵变之人不可学也。病名以千计,病症以万计,脏腑经络,内服外治,方药之书,数年不能竟其说,非勤读善记之人不可学也。又《内经》以后,支分派别,人自为师,不无偏驳。更有怪僻之论,鄙俚之说,纷陈错立,淆惑百端,一或误信,终身不返,非精鉴确识之人不可学也。故为此道者,必具过人之资,通人之识;又能摒去俗事,专心数年,更得师之传授,方能与古圣人之心,潜通默契。若今之学医者,与前数端,事事相反。以通儒毕世不能工之事,乃以全无文理之人,欲顷刻而能之。宜道之所以日丧,而枉死者遍天下也。
因此,古代对医学教育对象的选拔极为严格。长桑君考察扁鹊十余年方传其医术,罗知悌接受朱丹溪亦是进行多次考验。民间师徒授受如此,古代医学学校教育亦特别重视人才的选拔,招生制度极为严格。据《宋会要辑稿·职官》载:凡来学医者,年龄必须在15岁以上,首先要向太常寺投下家状,然后由召命官、使臣和翰林医官、医学一人作保、学生三人结为连保后方可在太医局试听。一年后经考核合格者才由太常寺给牒,补充为太医局的正式学生。地方医学、习医生徒亦需投纳家状,请命官一人作保、学生三人联保。清代汉族由六品以上同乡作保,旗人则由该官佐领作保,考察品德端谨、略通医理者,经面试合格后方准入太医院学习。这种招生制度基本上保证了学生的文化层次和人品,同时彰显了医学的严肃和审慎。
另外,古代选拔医学教育对象非常重视学生的医学基础,往往倾向于从医药世家中招生。元代规定医学考生主要从在籍医户及开设药铺、行医货药人家的弟子中选取合格者就读。明代实施世医制度,医官多世代承袭,医学生来源主要为医家子弟。清代袭明朝旧制,学生亦主要由医官子弟保送。医官子弟保送制度有其历史原因和时代背景,有其弊端所在,但家庭医学熏陶对学生医学的学习有着一定的帮助却是毋庸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