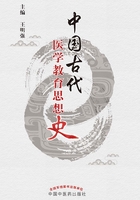
第二节 古代医学教育目的论与价值论
人类任何实践活动都有其目的指向和价值定位,否则就会失去存在的意义和前进的方向。医学教育亦然。医学教育作为培育医学人才的育人实践,其目的论和价值论赋予教育实践存在的意义,并对教学内容的安排、教学方法的选择等教育实践活动起着决定性的导向作用。
一、古代医学教育目的论、价值论管窥
古代医家对医学教育的目的与价值多有论述,他们在不同时代,受不同文化熏陶,从各个视角审视医学和医学教育,不断完善和充实医学教育目的与价值思想,使我国古代的医学教育目的与价值思想在多元中逐渐趋于圆融。
(一)《周礼·天官·冢宰》中折射出的医学教育目的与价值思想
《周礼》出现较晚,汉初尚无此书。西汉景帝、武帝之际,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征得一批古书,其中一部名为《周官》。献给朝廷后即深藏于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见焉”。直到汉成帝时,刘向、刘歆父子校理秘府所藏文献才重又发现此书,并加以著录。刘歆十分推崇此书,认为其出自周公手作。王莽时,因刘歆奏请,《周官》被列入学官,并更名为《周礼》。东汉时期,经学大师郑玄为《周礼》作了出色的注。由于郑玄崇高的学术声望,《周礼》一跃而居三礼之首,成为儒家的皇皇大典之一。关于《周礼》真伪和成书年代问题成为聚讼千年的一大公案,历代学者为此进行了旷代持久的争论,至少形成了西周说、春秋说、战国说、秦汉之际说、汉初说、王莽伪作说等六种说法。古代名家大儒,以及近代的梁启超、胡适、顾颉刚、钱穆、钱玄同、郭沫若、徐复观等著名学者都介入了这场讨论,其影响之大,可见一斑。《周礼》是一部官制汇编,是通过官制来表达治国方案的著作。抛开其成书年代不论,就是其确为西周时期周公旦所著,书中所载究竟是西周时期政治体制的实录,还是一部理想国的蓝图,目前尚无法确证。但无论怎样,《周礼》中所折射出的治国理念和思想是非常值得深入探究的。
《周礼·天官·冢宰》的《医师章》是对医疗卫生管理体制的构架。该书虽未明确表述医学教育的目的与价值,但其医官设置、职责和考核机制都折射出医学的目的与价值。如:
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供医事。凡邦之有疾病者、庀疡者造焉,则使医分而治之。岁终,则稽其医事,以制其食: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为下。
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
疡医……凡有疡者,受其药焉。
接受殷商暴政而亡的教训,周代非常注重施仁政、保万民。这种思想在其医官设置上亦有明确体现。其医疗对象不局限于服务王室贵族,而是面向“万民”,尽管对当时医疗服务对象的普及面到底有多大并无过多的文献去查证,但这种救济天下苍生的思想就已经使当时的医疗卫生体制散发出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光辉。再者,医疗以治病救人为根本宗旨,把医治疗效作为考核医生和制定俸禄的唯一依据。
医疗实践如此,势必会影响到医学教育。现无可靠的文献资料来考察周代的官办医学教育,倘其存在官办医学教育,其教育的目的和价值在于治病救人、保养万民应是无疑的。
(二)周代民间医生行医实践反映出的医学教育目的与价值思想
扁鹊(秦越人)是周代名医,是有信史记载的民间行医第一人。他长期行走民间,其治病对象,上至王公贵族,下至黎民百姓。《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载:“扁鹊名闻天下。过邯郸,闻贵妇人,即为带下医;过洛阳,闻周人爱老人,即为耳目痹医;来入咸阳,闻秦人爱小儿,即为小儿医。随俗为变。”扁鹊自始至终把治病活人、造福于人放在首位,而非以医追名逐利。他为昏迷的赵简子诊病,准确地判断出病情,“血脉治也”“不出三日必间”,并无挟病贪利之心。救治“已死”的虢国太子,名闻天下,“天下尽以扁鹊为能生死人”,面对赞誉,扁鹊并无邀名之意,而是实事求是地澄清事实:“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当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至齐,甘冒桓侯不悦,数次直言桓侯身病。
扁鹊经常带徒行医,《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就提到扁鹊指导子阳、子豹诊治病人。在授徒过程中,扁鹊是否言传治病活人的医学目的和价值思想不得而知,但其身教却会使这种思想更加深入人心。
(三)《黄帝内经》中的医学教育目的与价值思想
《黄帝内经》是我国医学宝库中现存成书最早、具备系统理论的医学典籍,确立了中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成为中国医药学发展的理论基础和源泉。《黄帝内经》虽无医学教育的专论,但不乏散见的有关医学教育的零言散语,且相关言论中也折射出医学教育思想。就医学教育的目的与价值而言,主要有两点。
1.传承医学
古代由于医生地位的卑微与遭受迫害、文字载体与出版手段的缺乏等,使得医学传承非常困难,因此《黄帝内经》中多次论述医学传承的重要性和神圣性,将之作为医学教育的首要任务。如:
黄帝问曰:余闻九针于夫子,众多博大,不可胜数。余愿闻要道,以属子孙,传之后世,著之骨髓,藏之肝肺,歃血而受,不敢妄泄。(《素问·三部九候论》)
帝曰:余闻九针,上应天地,四时阴阳,愿闻其方,令可传于后世,以为常也。(《素问·针解》)
帝曰:夫子之言,上终天气,下毕地纪,可谓悉矣。余愿闻而藏之,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昭著,上下和亲,德泽下流,子孙无忧,传之后世,无有终时,可得闻乎?(《素问·天元纪大论》)
2.造福百姓
《黄帝内经》的内容主要形成于周代,其受周代仁政思想影响非常明显,医学教育的要义在于传承医学,而传承医学的目的即在于保养万民、造福百姓。如《黄帝内经》中载:
帝曰:余闻得其人不教,是谓失道;传非其人,慢泄天宝。余诚菲德,未足以受至道,然而众子哀其不终。愿夫子保于无穷,流于无极,余司其事,则而行之,奈何?(《素问·气交变大论》)
黄帝问于岐伯曰:余子万民,养百姓,而收其租税。余哀其不给,而属有疾病。余欲勿使被毒药,无用砭石,欲以微针通其经脉,调其血气,营其逆顺出入之会。令可传于后世,必明为之法,令终而不灭,久而不绝,易用难忘,为之经纪。(《灵枢·九针十二原》)
(四)张仲景的医学教育目的与价值思想
张仲景,名机,字仲景,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被称为“医圣”。他在《伤寒杂病论·序》中提出了明确的医学教育目的与价值。
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
张仲景融合儒道二家思想,进一步充实完善了医学教育的目的和价值思想。“上以疗君亲之疾”是基于儒家忠孝思想,“下以救贫贱之厄”是出于儒家“兼善天下”的情怀,“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则是道教的养生保身思想。张仲景这种医学教育思想的形成有其时代背景:一是东汉末年社会动荡,战事频繁,疾病流行,张仲景的宗族“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二是道教的兴起。据史料分析,出生于河南南阳的张仲景深受武当山道教医药的影响,他在撰写《伤寒杂病论》时便引用了武当道教医药文献的宝贵资料《阴阳大论》和《胎胪药录》。
(五)葛洪的医学教育目的与价值思想
葛洪(284—364年)为东晋道教学者、著名炼丹家、医药学家。字稚川,自号抱朴子,晋丹阳郡句容(今江苏句容县)人。如果说张仲景受道教影响开始注意医学教育对个人自身的价值,那么葛洪则立足于个体赋予医学教育以新的目的与价值。
1.救己病痛,以得道成仙,长生不老
葛洪精晓医学和药物学,主张道士兼修医术,认为修道者如不兼习医术,一旦“病痛及己”,便“无以攻疗”,不仅不能长生成仙,甚至连自己的性命也难保住。对此,他多有论述。
神农曰:“百病不愈,安得长生?信哉斯言也。”(《抱朴子·极言》)
或问曰:“为道者可以不病乎?”抱朴子曰:“养生之尽理者,既将服神药,又行气不懈,朝夕导引,以宣动荣卫,使无辍阂,加之以房中之术,节量饮食,不犯风湿,不患所不能,如此可以不病。但患居人间者,志不得专,所修无恒,又苦懈怠不勤,故不得不有疹疾耳……是故古之初为道者,莫不兼修医术,以救近祸焉。凡庸道士,不识此理,恃其所闻者,大至不关治病之方。又不能绝俗幽居,专行内事,以却病痛,病痛及己,无以攻疗,乃更不如凡人之专汤药者。所谓进不得邯郸之步,退又失寿陵之义者也。”(《抱朴子·杂应》)
2.救护他人,以立上功
在葛洪看来,医学用于救护他人,是既利他又利己的事,其根本目的是为个人立功。
或问曰:“为道者当先立功德,审然否?”抱朴子答曰:“有之……为道者以救人危使免祸,护人疾病,令不枉死,为上功也。”(《抱朴子·对俗》)
(六)孙思邈的医学教育目的与价值思想
孙思邈,唐代著名道士,医药学家,被誉为“药王”。京兆华原(今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人。与道教学者葛洪不同,孙思邈深受佛家思想影响,具有舍身救世的情怀。其医学教育目的是“普救含灵之苦”,而不得有一己之私,否则就是“含灵巨贼”。他在《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中云:
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
(七)范仲淹的医学教育目的与价值思想
北宋范仲淹不仅是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对医学也很有见地。他的“不为良相,则为良医”(注:关于此语是否果为范仲淹之言,学界存有异议。参见余新忠《“良医良相”说源流考论——兼论宋至清医生的社会地位》,天津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的名言及施政实践大大提高了医学的地位。范仲淹不是以医家身份,而是从施政者的角度看待医学教育。他针对当时世俗之医多不经医授和医术不精的现状,大力倡导医学教育,目的在于培养合格的医学人才以救济世人。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任参知政事,上奏皇帝云:“今 京师生人百万,医者千数,率多道听,不经师授,其误伤人命者日日有之”“臣观《周礼》有医师掌医之政令,岁终考其医事,以制其禄。是先王以医事为大,著于典册”“选能讲说医书三五人为医师,于武成王庙讲说《素问》《难经》等文字,召京城习医生徒听学,并教脉候及修合药饵,其针灸亦别立科教授。经三年后,方可选试。高等者入翰林院,充学士祗应……所贵天下医道各有原流,不致枉人性命,所济甚广,为圣人美利之一也。”(《范文正公政府奏议·奏乞在京并诸道医学教授生徒》)
(八)李杲的医学教育目的与价值思想
李杲,字明之,真定(今河北省正定)人,晚年自号东垣老人,中国医学史上“金元四大家”之一,是中医“脾胃学说”的创始人。其医学教育目的为“传道”,而力斥“觅钱”,是为天下苍生计,而非为个人一己之私。《医史·东垣老人传 》载罗天益前往拜师,李杲见面即问:“汝来学觅钱医人乎?学传道医人乎?”确定罗天益求学为传道后,不但供其日用饮食,甚至资助银两贴补其家用,以使罗天益潜心学习。李杲传授医道的拳拳之心日月可鉴,令人敬仰。
(九)徐大椿的医学教育目的与价值思想
徐大椿(1693—1771年),原名大业,字灵胎,晚号洄溪老人,江苏吴江松陵镇人,清代乾隆年间名医。徐大椿医学教育目的在于传承“生人之术”,他在《医学源流论·自序》中云:“窃慨唐宋以来,无儒者为之振兴,视为下业,逡巡失传,至理已失,良法并亡,惄然伤怀,恐自今以往,不复有生人之术。不揣庸妄,用敷厥言,倘有所补所全者,或不仅一人一世已乎?”其对医学失传的忧患之情溢于言表。
纵览古代医学文献,在论及医学教育目的与价值时处处散发着心系生民、慈济天下的光辉,让人景仰。综合古代相关论述,我们可从不同的视角对医学教育的目的与价值作一归纳。
1.从医学传授者的视角:医学传承与济世利民相结合。
2.从学医者的视角:“保身长全”的利己思想与“慈济苍生”的利他思想相结合,而且绝大多数医家将“慈济苍生”居于首位,甚至不顾己利,一心赴救,更彰显出医学教育的光辉。
3.从治国者的视角:医学教育与仁政思想相结合。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古代医学及医学教育一向反对以医“谋利”。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指出:“医人不得恃己所长,专心经略财物。”《吴鞠通行医记》中强调:“良医处世,不矜名,不计利,此为立德。”费伯雄在《医方论·序》中更是明确提出:“欲救人而学医则可,欲谋利而学医则不可。我若有疾,望医之救我者何如?我之父母妻子有疾,望医之相救者何如?易地以观,则利心自澹矣!利心澹则良心现,良心现斯畏心生。”
二、对古代医学教育目的论与价值论产生影响的思想渊源
文化背景是实践理念产生的根源,古代医学教育的目的与价值论是在中国古代文化的基础上生发和完善的。概而论之,对古代医学教育目的论与价值论产生影响的思想渊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人命贵重思想
中国文化的精神特质,在于深体天地人合一之道。而在中国古代“天、地、人”的思维架构中,人是居于主导地位的,人才是整个宇宙的中心。许慎《说文解字》释“人”曰:“人,天地之性最贵者也。”段玉裁注云:“《礼运》曰:‘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又曰:‘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别声被色而生者也。’按禽兽草木皆天地所生,而不得为天地之心,惟人为天地之心,故天地之生此为极贵。天地之心谓之人,能与天地合德。”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产生了人贵论思想。《尚书·泰誓》中即云:“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将人看作万物之灵长。《荀子·王制》将万物分为由低到高的四个等级:“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本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
医学的产生是出于对生命的尊重,中国古代医学和医学教育的发达正是基于人为贵、人命至重的思想。《素问·宝命全形论》中即表达了为天地之间最为尊贵的“人”解除病痛的思想。“黄帝问曰: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君王众庶,尽欲全形,形之疾病,莫知其情,留淫日深,著于骨髓,心私虑之,余欲针除其疾病,为之奈何?”这种尊生贵命的思想历代医家多有论述。萧纲在《劝医论》中云:“天地之中,惟人最灵。人之所重,莫过于命。”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序》中解释自己将医著以“千金”为名云:“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其在《备急千金要方·治病略例》中云:“二仪之内,阴阳之中,惟人最贵。”
(二)儒家仁爱思想
“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对中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孔子首先把仁作为儒家最高道德规范,提出了以仁为核心的一套学说。仁的内容包涵甚广,《论语》中多次提到仁。《论语·颜渊》中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论语·雍也》中云:“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究其根本,“仁”的核心是爱人。仁字从人从二,也就是人们互存、互助、互爱的意思。
“医乃仁术”是中国古代医学本身的必有之义。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即认为“仁”为“医之本意”。明代医学家戴原礼在《推求师意·序》中明确提出“医乃仁术”。明朝王绍隆《医灯续焰》卷二十《医范》引陆宣公之言云:“医以活人为心。故曰:医乃仁术。”元代著名儿科医家曾世荣把自己的书命名为《活幼心书》,罗宗之在序文中赞云:“是心也,恒心也,恻隐之心也,诚求之心也。”明代裴一中在《言医》中谓:“医何以仁术称?仁,即天之理、生之原,通物我于无间也。医以活人为心,视人之病,犹己之病。”清代医家吴达在《医学求是》中云:“夫医为仁术,君子寄之以行其不忍之心。”清代喻昌在《医门法律·问病论》中云:“医,仁术也。仁人君子必笃于情。笃于情,则视人犹己,问其所苦,自无不到之处。”
另外,在古代医家看来,行医和行仁是合二为一的过程。晋代葛洪在《肘后备急方·序》中言:“岂止一方书而已乎?方之出,乃吾仁心之发见者也。”夏良心在《重刻本草纲目·序》中说:“夫医之为道,君子用之以卫生,而推之以济世,故称仁术。”在古代儒士看来,学而优则仕兼济天下能够造福百姓,除此之外最好的济世之途就是行医。宋代范仲淹提出“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人生理想。据北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一三《文正公愿为良医》载:“……他日,有人谓公曰:‘大丈夫之志于相,理则当然。良医之技,君何愿焉?无乃失于卑耶?’公曰:‘嗟乎!岂为是哉!古人有云: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能及大小生民者,固惟相为然。既不可得矣,夫能行救人利物之心者,莫如良医,果能为良医也,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民之厄,中以保身长年。在下而能及小大生民者,舍夫良医,则未之有也。’”而医术则是践行仁心的极好方式。正是这种“仁”的思想使古代医学焕发出无穷的魅力和勃勃生机,引领众多聪慧仁爱之士投身其中,使医学在“仁爱”的光辉下延绵不绝。许多读书人转而习医的心理动机和人生追求正是“医乃仁术”。朱丹溪早年“从乡先生治经,为举子业”,后来之所以“悉焚弃向所习举子业,一于医致力焉”,正是认识到“士苟精一艺,以推及物之仁,虽不仕于时,犹仕也”。其云:“吾既穷而在下,泽不能致远,其可远者,非医将安务乎?”可以说是与范仲淹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医家以“仁”学医、行医、传医,而治国者则从施仁政的角度发展医学和医学教育,“保养万民”“济世救民”的治国理念使得中国古代的医学和医学教育一直走在世界前列。
(三)道家重生思想
儒家虽亦倡导“独善其身”,但是在“兼济天下”不可得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因此,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医家多以“济世救民”为首,甚至主张“舍生取义”。而道家却为医学寻找到个人目的和价值。
“贵身”是老子的一种重要思想。他认为,人存于天地之间,与道、天、地并为域中四大之一。《老子》第二十五章云:“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主张要宠辱皆忘,不要为追逐名利、荣辱、得失等身外之物而伤身,认为只有真正懂得贵身爱身的人才可以将天下托付给他。《老子》第十三章云:“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庄子》一书中“重生”思想更是其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主张摆脱一切外在物累,从而获得生命的张扬。庄子极力反对因外物而损耗生命,即使是整个天下也无法与生命的宝贵相比拟。其云:“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况他物乎”“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异乎俗者也”(《庄子·让王》)。天下尚且不足以让人为之衰耗生命,更何况他物呢?《让王》中云:“以随侯之珠弹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则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轻也。夫生者,岂特随侯之重哉!”如果有人用随侯宝珠去射飞得很高的麻雀,世人一定会嘲笑他,为什么呢?因为他所用的贵重而所求的轻微。生命,岂止随侯宝珠那样珍贵!名位利禄正如高空的鸟雀,而人的生命却是远比随侯宝珠珍贵得多,因此因名位利禄而伤生实在是得不偿失。所以,大智慧的人宁愿安贫乐道,也是不会因外在的东西而给自己带来伤害的,“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审自得者失之而不惧,行修于内者无位而不怍”(《让王》)。
道家对自身生命的重视远超过儒家,把生命看作人生的第一要义,弥补了儒家利他思想的缺陷,赋予医学以利己价值和意义,完善了医学的目的和价值论。当然,这种高度重视生命的思想对医学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积极的影响。以人为本、尊重生命是中医医德最重要的思想基础和最突出的人文特征,救死扶伤是医生的神圣职责,医生必须重视人的生命、珍视人的生命。
(四)佛家悲悯情怀
佛教于东汉末年自印度传入,填补了中国本土文化的缺憾,在儒家入世思想、道家玩世思想之外添加出世思想,使得中国文化得以实现圆融。佛教传入中国后,努力与中国本土文化相融合,很快得以广泛传播。佛教慈悲为怀、普度众生、众生平等思想给医学带来很大影响。尤其要指出的是,古代医学深受儒家“仁爱”思想影响,但是儒家之“仁爱”是建立在“亲亲”基础上的,强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爱是有差等的。佛家众生一等的思想弥补了儒家思想的此种缺陷,在佛家思想影响下,医家之“仁爱”超越儒家的“亲亲”原则,而“誓愿普救含灵之苦”,无论何等人前来求医,都要“如至亲之想”。
古代许多医家深受佛家思想影响,甚至一些僧人本身就身兼医工。他们以悲悯的情怀看待世人,以医学为普救世人的手段,赋予医学以悲天悯人、普救苍生的大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