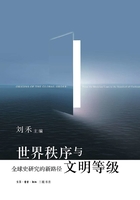
∷ 文明论:一个泛学科的政治无意识
文明等级论——简称文明论——成为全球史研究的一个关键,究其主因,还是因为它在许多学科里充当着“政治无意识”的角色。长期以来,这个角色独特的泛学科属性,可能是造成文明论的研究被学科的藩篱挡在门外的直接原因,但忽略和遗忘,恰恰突出了文明等级的意识形态作为“政治无意识”的强大功能。它像空气一样,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
这种意识形态的深刻性体现在文明论与现代学科的历史同构之中。人们所熟悉的现代学科——以文科和社会科学为主的研究领域,还有诸多科学分支,如进化论生物学、体质人类学、优生学等——与文明论的产生和发展分享同一个历史进程,两者之间有着极其密切的往来和相互渗透。这一历史进程,主要指的是从欧洲开始的资本主义殖民体系在全球的推进和扩展,以及与其同步发展的各现代学科。
现代学科的建立与资本主义殖民体系的历史渊源触及方方面面。本书涉及的学科有政治经济学、地理学、人类学、人种学、国际法、语言学、历史学等。其中,地理学家唐晓峰在论集的开篇,为读者了解现代地缘政治的历史脉络设定了基础性的坐标。他指出,所谓地理大发现,其实就是一场“文明”大发现。欧洲人在海外探险的过程中,将分布在空间的人群差异整理为历史的差异,也就是把空间的分布诠释为时间的分布,又将时间的差异解释为文明进化程度的差异。由此,现代地理学的诞生获得了有力的解释,这个学科自始至终都参与着对文明等级话语的塑造。唐晓峰的结论是,文明论是一种新的历史眼光,现代地理学正是基于这种眼光,为欧洲建立了新的人文世界的想象。
地理大发现后,陆续诞生了政治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欧洲文明史、国际法等,它们全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对文明等级论的塑造。以著名的社会阶段论(stages of society)为例,18世纪法国的重农学派率先提出三个社会阶段的模式,把人类社会描述为狩猎、游牧、农耕的由低到高的发展模式。接下来,苏格兰启蒙主义思想家亚当·斯密又提出一个完整的四个阶段论,即狩猎、游牧、农耕、重商,从而将资本主义的发展加入了社会发展阶段的描述。
启蒙主义思想家提出的社会阶段论,为政治经济学提供了进步主义的思维方式,同时也为文明等级论打下了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瑞贝卡·卡尔(Rebecca Karl)在为本书撰写的文章中,回顾了历代经济史学家围绕“亚细亚生产方式”进行的长期争论,指出了这些讨论的盲点所在:实际上,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说法,只有在社会阶段论的框架内才有意义,但是有能力克服这个盲点的经济史学家并不多,王亚南即是其中之一。这位中国经济史学家认为,传统中国社会经济的所谓特殊性,并不外在于人类普遍历史的范畴,他也不承认其他东方国家有什么“亚细亚的生产方式”,这无异于给社会阶段论本身打上一个问号。我们下面还会看到,进步主义历史观的出现,究竟给经典的文明等级标准带来了哪些思想资源。
本书收入的多篇文章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近代形成的文明等级论做出了详细的考察和分析。梁展将文明论的谱系置放在知识考古的聚光灯下进行了系统的剖析,比如他对福柯所言的国家理性的再度思考,对德国生理学家布鲁门巴赫的人种分类法,以及生理学家爱德华斯人种学做出的新评价,这一切都让读者发现文明等级论的另一张面孔——它凭据肤色和其他的种族特征,在欧洲18世纪新兴的科学种族主义实验中,一跃变成科学研究的前沿,成为那个时代的显学。在这个基础上,梁展为我们梳理了晚清诸人编译的欧美国家的文明等级标准,尤其是政治地理教科书这个扩散全球的传播渠道。在他提出的解释框架中,康有为的种族改良计划和大同世界,也获得了新鲜独特的诠释,它让我们看到,《大同书》与文明等级论的传播竟有如此不可分割的联系。这给我们最大的启发是,晚清中国产生的思想必须放在全球史的视野中才能得到充分的解释。
什么是经典的文明等级标准?
欧美人塑造的文明等级含有一套由低到高的排列标准,这套标准将世界各地的人群分别归为savage“野蛮的”、barbarian“蒙昧/不开化的”、half-civilized“半开化的”、 civilized“文明/服化的”以及enlightened“明达的”(今译“启蒙”)五个等级,除此之外,还有三级之分(野蛮、蒙昧、文明)和四级之分(野蛮、蒙昧、半开化、文明)。无论五级、四级还是三级,这套文明等级的标准起初并不严格,不过,经过几个世纪的沿革和变化,它慢慢地趋向稳定,及至19世纪初,形成了一套经典化的论述,被编入国际法原理,被写进政治地理教科书,被嵌入欧洲国家与其他国家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最后形成欧美国家认识世界的基础。
文野之分——近代对文明与野蛮的区分——是国际法的思想基础,这一点是我们理解现代世界秩序的关键之一。换句话说,不了解文明等级的标准何时产生,为什么产生,我们就不可能真正懂得为什么在欧洲会出现一个国际法,而这个国际法自始至终都与统治世界有关。我为本书撰写的文章,旨在把国际法的思想脉络整理清楚,清理的重点不是针对法理本身,而是为了充分剖析现代国际法的地缘政治,特别是前面说到的那个双重结构的地缘政治的出现和生长。因此,文章虽然也涉及国际法通常所面对的那些领土争端和国家主权问题,比如野蛮人的“无主荒地”问题,或者半文明国家被迫接受“领土割让”的条款等,但我集中探讨的是,现代世界秩序的道义是如何伴随着国际法原理的发明而得以呈现,依此争得人心,并取得全球共识的。比如,欧洲文明国家占有“野蛮人”土地的合法性在哪里?为什么国际法允许文明国家对“半开化”国家实行治外法权,而不允许文明国家之间实行治外法权?这里的义理是什么?它如何自圆其说,以至于就连被征服者都感到心悦诚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