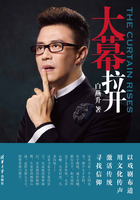
想回河北台
在总编室的三个月,备受煎熬。我对自己是否还要继续干电视都产生了怀疑,也没有了在中央台干下去的信心,一度想回到河北台。
俗话说,好马不吃回头草。我无数次地劝慰自己:再忍忍!
孙小梅从美国探亲回来后,我们俩又共同主持了一期《电视你我他》,是我在总编室的最后亮相,如日中天的小梅回来了,我自然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感谢当时人事处的领导王晞建。1993年12月份,是他到河北台亲自商讨我的调动事宜,这次,他又亲自带我来到文艺部办公室,把我安顿下来。我成了《文艺广角》的主持人,和桑艳、肖丽轮流搭档。
《文艺广角》是当时最长的栏目,上半部分是一小时的专题类节目,主持人访谈嘉宾串联节目,下半部分是一个半小时的《广角剧场》,负责播出各种不同类型的晚会。
记得有一次,邀请了京剧名家李维康、耿其昌夫妇做嘉宾,他们是我非常喜爱的艺术家,他们的演唱炉火纯青,舞台呈现气定神闲,堪称大家。我至今都认为,中国京剧院有两位新时期的划时代大青衣,一位是杜近芳,一位就是李维康。杜近芳老师的美不知让多少人倾倒,李维康老师独具匠心的演唱称之为“李派”也不为过,只是她没有广收弟子。
后来和李老师熟了,我问她,为什么不收徒弟?李老师开始只是笑,摇头不语。在我的再三追问下,她说:我对艺术很尊重,对自己很严,自然对收学生严上加严,我不能误人子弟。
我还是不满足,继续追问,您觉得青年演员中谁条件不错?她告诉我:山西的李胜素不错!
那会儿,李胜素还没有什么名气。可以说,是李维康老师的回答和评价让我对胜素有了重新认识。
又想起这之前我去袁世海先生家采访,我以同样的问题问他:您觉得中国京剧院的青年女演员中谁条件不错?他脱口而出:刁丽!可惜啦。
刚走进电视戏曲的我,想快速了解评判人和戏,除了自己多看多思之外,捷径之一,就是多向大家发问讨教。
主持《文艺广角》期间,1995年的“五四”专辑,是在北京大学校园采访录制的。十几个北大学生,书生意气慷慨激昂,让我备感青春。之后我们又邀请了表现出色的一男一女两位同学来到电视台演播室,和我共同录制这期“五四”专辑串联,那位女生给我留下较深印象,个性倔强不算亲和,但思维敏锐表达流畅,挺适合吃主持人这碗饭的。
她毕业后,果然来到了中央电视台,在2008年的抗震救灾报道中,出色完成了“向世界报道”的任务。她,就是当年的那个女生——张泉灵。
因为《文艺广角》是周播节目,对于无牵无挂一门心思只想干活儿的我来讲,忙不起来,闲着难受。于是伺机寻找另外的舞台。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半边天》的负责人孙素平和穆晓方,当时《半边天》只有三位女主持,我自告奋勇地说,想主持《半边天》,两位领导居然答应了。就这样,我成了《半边天》第一位男主持,主持了近半年。记得当时北京某报还在头版刊登了对我的专访《女儿国里的半边天》。
记不清后来是怎么离开《半边天》的,但那段时间很愉快,工作量不大,就是演播室录个串联,因为不用我外出采访,所以也不影响《文艺广角》的录制,最主要的是我的老父亲可以看见一套播出的《半边天》。
没正式获得中央电视台身份的这段“漂泊”日子,挣扎无助煎熬难耐。动荡不安中,更多的是苦闷,欢乐的时光难寻。很长一段时间,我坚信这样一个公式:天赋+机遇+勤奋=成功。事实上,在中央电视台这个中国最大的名利场和绞肉机里,想保持真诚、想出人头地,面临的现实远比那个成功公式艰难复杂得多。后来渐渐明白,一个人是否成功,是否快乐,有运气因素,但通常都取决于我们的选择和面对现实的心态。
到中央台一年多的跌跌撞撞,让我预感到接下来的路同样不好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