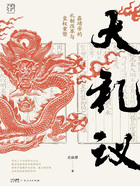
三、左顺门事件
嘉靖元年三月十五日(壬戌),嘉靖皇帝下诏:“大礼”议定,不得争论。(180)并赏赐定策、迎立及兴藩随行诸臣,封阁臣杨廷和、蒋冕、毛纪为伯爵。(181)可是,杨廷和等人有感于“英主恩谊讵易消受,况群怨日眈眈其侧”(182),坚拒恩典,否则将辞官避位。(183)嘉靖皇帝无奈,收回成命,改封赏为荫子。这时,“大礼议”似已圆满落幕,君臣关系又恢复融洽的状态。实则不然。“大礼”引发的风波还未结束,嘉靖初年的政局暗潮汹涌。从下列的事例来看,嘉靖君臣因“大礼议”留下的心结没有解开。(184)
例一,嘉靖元年三月三日,礼部请求上兴献帝册宝时不用乐,以别皇帝谥册典礼。(185)嘉靖皇帝答应礼部,但要求“兴献帝册文还宜称孝子”(186)。杨廷和率阁臣上疏:册文已清楚表明嘉靖皇帝是兴献帝亲子,不须再特别指出。皇上已继统孝宗,不宜再对本生父亲称“孝子”,避免二父之嫌。嘉靖皇帝扣留此疏,不作回应。(187)
例二,据《皇明嘉隆两朝闻见纪》记载,嘉靖皇帝曾私下派出太常寺丞周璧(原兴藩的典仪副)前往南京,转告张璁“诏虽下,圣心未慊也”(188),暗示张璁等待时机,再议“大礼”。史料阙漏,无从判定真伪,却显示嘉靖皇帝并非真心接受“濮议论”。同时,支持张璁论点的官员也越来越多。例如,巡抚湖广右副都御史席书、吏部员外郎方献夫(?—1544)皆曾具疏支持“人情论”(189),但担心被言官弹劾,只能静待“大礼”再起之时机。(190)
例三,嘉靖元年十一月二十日,南京礼部尚书杨廉(1452—1525)等人上疏,劝嘉靖皇帝赶紧选择兴献帝的嗣子人选,主持兴献帝的祭祀典礼,申明“大礼”,平息众议。嘉靖皇帝不置可否,奏疏留中,命礼部商议。(191)
例四,嘉靖元年十一月十八日,寿安皇太后邵氏病死。为让祖母邵太后能风光入殓,嘉靖皇帝命礼部拟定徽号,举行隆重的丧礼,坚持让邵太后入葬茂陵,与宪宗成化皇帝合葬。礼部尚书毛澄不敢力争,交由内阁处理。杨廷和等人则大力反对,说明邵太后本是宪宗之妃,并非皇后身份,自然不得归葬茂陵。若欲归葬,将惊动宪宗神灵,破坏祖坟,应葬于皇太妃原葬地橡子岭。(192)嘉靖皇帝不予理睬,无视明朝一帝二后墓葬礼制(193),坚持归葬茂陵,为祖母争一份死后的尊崇,使她拥有皇太后的实质身份,成为宪宗的第三位皇后,无形中让兴献王的政治身份升高到“皇后之子”和“宪宗嫡子”的地位。
例五,嘉靖二年(1523)四月,宦官蒋荣(原兴藩人马)奉命掌管兴献帝陵祭,上疏请礼部择定祭品及乐舞规格。礼部据凤阳祖陵之例,用笾豆十二,不设乐舞,并请选宗室亲王主祭。嘉靖皇帝四次驳回礼部方案(194),直接下诏让兴献帝家庙“乐用八佾”。“八佾”是天子专用的乐舞仪式。嘉靖皇帝亲定乐舞仪式的目的即排除礼部,直采八佾之乐,让兴献帝享用天子祭礼之殊荣。(195)
嘉靖二年是言官交相攻击、风言闻事的一年。(196)科道之风盛行,显示了内阁首辅杨廷和再也无法控制言路,言官们锋芒大露。(197)科道之风,始于兵部给事中史道(正德十二年进士)私怨杨廷和,因而借“大礼”为由,上疏弹劾杨廷和欺罔,欲陷皇帝于不孝之名。(198)这道弹劾奏疏引起众怒,“一时大小臣僚无不为杨疏辨”。(199)嘉靖皇帝怀疑朝臣党附于杨廷和,开始猜忌杨廷和的忠诚。
兵部尚书彭泽(弘治三年进士)也挺身而出,为杨廷和辩驳,指责史道无的放矢。未料却引起言官们的不满,纷纷批评彭泽堵塞言路,企图遮蔽皇上的耳目。(200)御史曹嘉(正德十二年进士)也抨击杨廷和阁权太重(201),“能擅威权,以移主柄”(202),揭露正德朝的施政过失(203),让嘉靖皇帝更怀疑杨廷和实有私心,欲借“大礼”窃夺皇权。换言之,言官们展开了喋喋不休的批评,内阁与六部尚书纷纷称疾不出,以示清白,朝政顿时停摆,引起嘉靖皇帝的不满。不久后,言官们又把矛头转向皇帝,要求疏远佞臣崔文,立即罢斥;又指责嘉靖皇帝迷信方术,不应在宫中举行斋祀。(204)言官多有过激,嘉靖皇帝虽不加罪,但逐渐失去了包容言官的耐心。(205)
从这些冲突来看,嘉靖皇帝越来越不满杨廷和,也越来越厌烦言官们无止境的谏言(206),于是对朝廷重臣们的态度大为转变。凡有人提出请辞(207),嘉靖皇帝便准许他们退休回乡,不再苦苦挽留。杨廷和由于一直坚持“濮议论”,与嘉靖皇帝之间的芥蒂越来越深,又频劝嘉靖皇帝不可笃信斋醮,语多冲撞,让嘉靖皇帝“忽忽有所恨”。(208)事隔不久,杨廷和又因添派织造太监事,发动公论(209),希望借舆论压力,让嘉靖皇帝再次撤销命令。但嘉靖皇帝坚持己见,不予理会。朝廷里的气氛转为紧张。
正在这敏感的时刻,南京刑部主事桂萼因常与张璁私下讨论“大礼”,揣测嘉靖皇帝的心意,实不愿接受“濮议论”,因而请求重议“大礼”。桂萼重申“人情论”,主张应称兴献帝为皇考,改兴献后为圣母,称孝宗为皇伯考,称昭圣皇太后为皇伯母,并在皇宫里为兴献帝立家庙祭祀,直接由嘉靖皇帝亲自祭祀,始符合人情。(210)桂萼担心自己势单力薄,不足以撼动朝廷,于是将南京兵部右侍郎席书及兵部员外郎方献夫先前未上的奏疏,一并附于奏疏之末,希望得到嘉靖皇帝的重视。同时,“人情论”的提出者张璁,也跟着桂萼上疏,请求再议“大礼”。嘉靖皇帝十分高兴,越发想重议“大礼”,提高兴献帝的地位,于是将张璁、桂萼等人的奏疏交给礼部商议。
嘉靖皇帝重议“大礼”的举动,让杨廷和心灰意冷,不得不下台求去。(211)嘉靖皇帝不但不挽留,还召回张璁、桂萼、席书等人,希望借由他们的支持,驳倒“濮议论”。嘉靖皇帝为兴献后蒋氏祝寿时,特别把寿宴办得十分盛大,却对昭圣皇太后的寿辰不闻不问,甚至以懿旨有命为由,免除百官朝贺。嘉靖皇帝厚此薄彼的做法,引起言官的不满,言官屡有进谏。嘉靖皇帝大怒,下令锦衣卫逮捕这些言官,予以拷问,开嘉靖朝杖责言官之劣风。(212)
杨廷和致仕后,蒋冕继任首辅,与礼部尚书汪俊、吏部尚书乔宇等人成为“濮议论”的中坚分子。(213)嘉靖三年二月十三日(戊申),礼部尚书汪俊会同朝臣二百五十余人重申“濮议论”,抨击张璁、桂萼狂妄,“故继主于大义,所生存乎至情”。(214)嘉靖皇帝不予理会,反而命张璁等人尽快进京,以便商议“大礼”。
综合嘉靖皇帝的举动及前后种种迹象,嘉靖皇帝非争“大礼”不可的意图显现。(215)不久后(三月一日),嘉靖皇帝便以孝心未尽为由,重议“大礼”,要求礼部加称尊号,“兴献帝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兴国太后为本生母章圣皇太后”(216),并命宦官前往安陆兴藩,迎兴献帝神主,欲在皇宫内院的奉先殿侧建观德殿,充当家庙,以便祭祀。(217)这项命令一出,朝议哗然,众臣纷纷上谏劝诫。(218)但嘉靖皇帝皆不理会,将上谏者停俸,同时也下令礼部,改兴献帝陵墓为“显陵”,祭祀仪制抬高为天子之祭。(219)
礼部尚书汪俊为维护“濮议论”的基本立场,又见嘉靖皇帝将重议“大礼”,因而召集群臣,请与嘉靖皇帝妥协,让兴献帝尊号加称“皇”字,希望能满足嘉靖皇帝,不再坚持称兴献帝为“本生皇考”。(220)嘉靖皇帝本想作罢,不再多生事端,但此时又接获张璁的奏疏,疏中分析“加称不在皇不皇,实在考与不考”(221),表示不与“濮议论”妥协的立场,力劝嘉靖皇帝拒绝礼部的方案。对此,嘉靖皇帝深以为然,立刻表明不愿接受汪俊的提议,直接下诏决定“兴献帝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兴国太后为本生母章圣皇太后”。(222)张璁、桂萼又上疏,请去“本生”字样:兴献帝的尊称虽有“本生皇考”,但仍无法表明兴献帝的身份,“曾有一人两考之礼乎”。(223)若不去掉“本生”二字,兴献帝仍会被视为“皇叔”,而非“皇考”。(224)礼部尚书汪俊受挫后,便因反对观德殿的兴建遭到罢免,使主张“濮议论”的一方元气大伤。
尤有甚者,嘉靖皇帝不理会吏部的廷推结果,特旨授命南京兵部右侍郎席书担任礼部尚书,使主张“人情论”的一派实力大增,可以左右礼部廷议的结果。尽管如此,持“濮议论”的人士,如吏部尚书乔宇、九卿与言官群体,批评张璁、桂萼等人的攻势仍旧猛烈,频频上疏论辩,并会同群臣上奏《建室议》,反对建观德殿,要求惩处张璁等人。面对众多朝臣的反对意见,嘉靖皇帝先是婉转述说自己只是想尽孝道,请言官们不要为难。但言官仍不为所动,继续弹劾张璁等人,让嘉靖皇帝越来越无法忍受,君臣关系恶化,冲突日益尖锐。
到了五月,首辅蒋冕以老病乞休为由,试图劝阻“大礼”之议。嘉靖皇帝大怒,立刻罢免蒋冕,还责骂他多次乞休的行为“非大臣事君之义”。(225)又亲下手诏,破格任命张璁、桂萼为翰林学士,方献夫为侍讲学士。这项特殊的任命,引起翰林院诸臣极度不满。特别是杨廷和之子、翰林院修撰杨慎更为愤怒,于是鼓动三十六名翰林学士,联名上奏,表示翰林院众官羞于与张、桂等人为伍,愿请辞官回乡。同时,翰林院修撰吕柟(1479—1542)、编修邹守益(1491—1562)亦上疏力谏,请罢兴献帝称考与大内立庙二事。(226)嘉靖皇帝十分气愤,令锦衣卫逮捕吕柟与邹守益二人,严刑拷打,谪降边地。(227)
吏科都给事中李学曾(弘治十五年进士)等二十九人、河南道监察御史吉棠(正德九年进士)等四十五人则代表言官意志,联合上疏“萼等皆曲学偏见,紊乱典章”(228),请求嘉靖皇帝予以惩罚。御史段续(嘉靖二年进士)、陈相(正德十二年进士)“极论席书及萼等罪状,请正典刑”。(229)面对雪片般涌入的弹劾奏疏,嘉靖皇帝不再容忍,怒责言官,命他们申辩己罪,还以欺罔妒贤的名义,逮捕段续与陈相二人,交由北镇抚司拷问。吏部员外郎薛蕙(正德九年进士)更为激烈,上《为人后解》二篇,明言大宗小宗之别,再作《为人后辩》一篇,说明“大宗不可绝”的理由——“继祖体而承适统,合于为人后之义,坦然明白”(230),规劝嘉靖皇帝接受自己的嗣子身份,不要再议“大礼”,破坏国家礼法。(231)后又有鸿胪寺右少卿胡侍(正德十二年进士)等人弹劾张璁为奸邪小人,必须罢劾。嘉靖皇帝不听,反而处罚这些言官,皆予谪官夺俸。
从这一连串的冲突来看,可知嘉靖皇帝的态度日益固执,张璁、桂萼等人与“濮议论”的支持者之间,对立也越来越分明,让“大礼”日趋激烈,进而升级为君臣间的政治斗争。到了七月,“大礼议”已达白热化,进而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史称为左顺门事件。(232)
七月十二日(乙亥),嘉靖皇帝下谕礼部:“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更定尊号,曰圣母章圣皇太后,于七月十六日恭上册文遣官祭告天地、宗庙、社稷。”(233)内阁大学士毛纪、费宏接到诏令后,大惊失色,纷纷表示反对,并向皇帝谏言,“本生二字,上干宗庙,内干宫闱,事体重大”(234),希望嘉靖皇帝收回诏令。朝廷官员也纷纷上疏,劝阻皇帝,甚至表示不愿参加册封典礼(235),坚持去“本生”二字。但张璁和桂萼两人却一同上疏,列举礼官欺罔十三事(236),批评支持“濮议论”的朝臣是朋党、是小人,应予以治罪。嘉靖皇帝不愿意引起朝政动荡,留中所有的奏疏。
七月十五日(戊寅),按例于奉天门召开早朝。吏部左侍郎何孟春(1474—1536)见嘉靖皇帝留中所有奏疏,惶惶不安,欲趁早朝议事的机会,袭用成化朝的故事(237),制造舆论压力,让嘉靖皇帝收回旨意。于是翰林院检讨王元正(正德六年进士)及张翀(正德六年进士)等人在金水桥拦住刚下早朝的官员们,振臂大喊:“万世瞻仰,在此一举,今日有不力争者,当共击之。”(238)素有清望的杨慎也呼吁:“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239)在杨慎等人的鼓动下,共召集了二百二十多位大臣伏跪左顺门外,欲行哭谏,甚至还高呼“高皇帝”“孝宗皇帝”的名号,群情激动。嘉靖皇帝不得不软化态度,数次派出司礼监太监安抚伏阙诸臣的情绪,命他们先行退去,否则将处违反朝仪之罪。可是伏阙诸臣不听,还要求阁臣毛纪等人一同在左顺门跪伏。内阁首辅毛纪听到消息后,便带头跪伏,试图挽回皇帝的心意。直到中午,整个跪伏行动持续扩大,气氛更为昂扬,反而聚集了更多的官员。

被群臣拒绝的嘉靖皇帝感到非常难堪,认为朝臣的集体跪伏是要挟手段,也是对皇帝权威的反抗,于是改采强行镇压的手段。先命司礼监太监记下伏阙诸臣的姓名,再派遣锦衣卫逮捕伏阙行动的首谋者,翰林学士丰熙(弘治十二年进士),给事中张翀,御史余翱(正德六年进士),郎中余宽(正德六年进士)、黄待显、陶滋(正德九年进士)、相世芳(正德九年进士)及大理寺正毋德纯(正德十二年进士)等八人皆收押入狱。(240)杨慎等人见状,十分愤慨,不禁用力拍打左顺门的大门,放声大哭,哭声竟震动宫廷,场面失去控制。嘉靖皇帝听到杨慎等人的哭喊声,更加震怒,再命锦衣卫强制驱离左顺门的群臣,并逮捕马理等一百三十四人,将之下狱,勒令四品以上的八十六名官员在家待罪、听候发落。
面对嘉靖皇帝的雷霆之怒,吏部左侍郎何孟春仍想挽回劣势,借助通政司官员的协助,再度上疏反驳张璁的《正典礼第七》(241),辨明自己和伏阙诸臣并非朋党,请嘉靖皇帝勿信谗言。何孟春求助通政司的举动,不只犯下偷窥奏疏之罪(242),也让嘉靖皇帝怒责何孟春:“结众口为朋俦,因私忿而伤大体,岂大臣事君之道。”(243)他更怀疑伏阙诸臣的动机,认为朝廷之内必有朋党,企图干预皇权的独断。并申诫通政司,不得再让他人窥探奏疏,违者严惩不贷。(244)经过这次事件,嘉靖皇帝外放何孟春为南京工部左侍郎,切断其人事纽带,沦为赘员(245),使其不得再争论“大礼”。七月二十日(癸未),嘉靖皇帝让锦衣卫立即审讯,指责伏阙诸臣“以忠爱为由,实为欺党,私朕冲年,任意妄为”(246),并流放丰熙等八名伏阙领袖,四品以上官员停薪,其余一百八十多位官员遭杖刑,翰林修撰王相(正德三年进士)、王思(正德六年进士)等十七人惨遭杖死。(247)嘉靖皇帝仍没有消气,特别下令将杨慎、王元正及给事中刘济流放充军,安盘等人俱削籍为民,主张“濮议论”的骨干成员几乎被罢斥殆尽,奠下“人情论”获胜之基础。
何孟春等人被外放后,张璁、桂萼等人开始得势,一面大力鼓吹“人情论”,屡次建议改称孝宗皇帝为“皇伯考”,以正献皇帝“皇考”之名;一面寻求支持己方的势力,暗中结交武定侯郭勋,给事中陈洸、史道,以及御史曹嘉等人,借他们打击“濮议论”的势力。(248)同是“人情论”支持者的霍韬、席书及方献夫等人,也先后上言:“三代之法,父死子继,兄终弟及,人无二本。孝宗,伯也,宜称曰皇伯考;昭圣,伯母也,宜称曰皇伯母;献皇帝主,别立祢室,不入太庙,尊尊亲亲,两不悖矣。”(249)
然而,朝堂上仍有不少“濮议论”的支持者,如吏部侍郎汪伟(弘治九年进士)、兵部右侍郎郑岳(1468—1539)、大理寺左少卿徐文华(正德三年进士)等人。同样主张“濮议论”,但立场较不明显者,如大学士费宏、石珤等人也公开反对嘉靖皇帝。(250)但“濮议论”已成强弩之末,发挥不了作用。武定侯郭勋则公开支持张璁等人,礼部尚书席书更加露骨地说“人臣事君,当将顺其美”(251),终于让“大礼”拍板定案。嘉靖三年九月五日(丙寅),嘉靖皇帝独断“大礼”,不顾反对舆论,直接下诏“称孝宗敬皇帝曰皇伯考,昭圣皇太后曰皇伯母,恭穆献皇帝曰皇考,章圣皇太后曰圣母”。(252)九月十五日(丙子),颁布天下。(253)大礼议的第一阶段,即兴献王尊称之争,终画下句点,结束长达三年的“大礼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