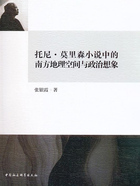
二 女性身体实践与主体性建构
(一)伊娃的身体暴力与匹斯女性王国
身体暴力如同对身体的驯服一样,通过对身体样貌的改造或变形以达到某种目的。中国封建社会女人裹脚便是一种典型的身体实践,这种实践通常是在主体的知会或同意下,由家中年长女性对适龄女性实施的一种实践,目的是使年幼的女性符合社会(尤其是男性)对她们身体的要求,行为本身为了迎合社会对女性形象的审美要求和角色塑造。无论是被动实践还是主动实践,身体暴力实质上是一种对主体的安置[18],主体通过被摧残或改造的身体来达到某种目的。
伊娃主动选择“断腿”是对“底部”黑人艰辛生活的反映和对抗。伊娃·匹斯是秀拉的祖母,小说中女性的反抗及主体性建构始自年轻时的伊娃。伊娃新婚后跟随丈夫波依波依从弗吉尼亚搬迁至梅德林,后丈夫弃她和三个孩子而去。伊娃无以为生,便用自己的一条腿换取了政府的保险金。“有人说,伊娃把腿放到火车轮下轧碎了,然后要人家赔偿。也有人说,她把那条腿卖到医院,整整卖了一万美元。”(34)后现代小说不确定的表述策略为伊娃的身体实践增加了某种神秘色彩,使得主人公的经历更具传奇性。独自带着三个孩子,没有任何收入的伊娃陷入了无法解决的困局。在消失了一段时间后,伊娃带着一份稳定的保险金回到梅德林,开始认真地抚养孩子。无论是哪种方式,伊娃在困境面前主动对自身身体实施暴力的做法是对“底部”黑人生活的控诉。不同于奴隶制时期白人对黑人进行的各种身体戕害,黑人的自我施暴更是一种自觉的命运反抗。黑人没有和白人平等竞争工作的机会,普遍的歧视和权力链条将他们牢牢锁住,就像裘德一样,多次努力却仍然无法突破原有的生活轨迹。伊娃的反抗使她在逆来顺受的黑人群体中获得了一个崭新的形象,展现出一种鲜见的黑人生活日常。这种通过对身体实施自我暴力的另类日常实际上是对常规、沉默和权力的挑战,是一种突出的解域化实践。
如果说伊娃被迫“断腿”是对现状的控诉,那么她对身体残缺的固守和自我幽禁则是自我赋权和女性独立的一种宣言。在人类历史上,女性一直被塑造为柔弱的、依赖于男性的,甚至被商品化进而成为消费对象。伊娃也不可避免地落入了社会为女性制造的窠臼,一度对男性充满依赖并以其为家庭的核心,女性主体性丧失。当丈夫数年后再露面的时候,伊娃不知道怎么面对。“心怀对波依波依的恨,她就能坚持下去,只要她想或者是需要借助这种恨意来确认和强化自己。”(40)尽管伊娃做出了特立独行的姿态,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对丈夫或者其他男性的看法仍然带有一种传统赋予的角色和道德追求。伊娃通过“恨”来保持和强化自我,这实际上是一种“二手”的自我,它的确立还是基于男性存在的。尽管如此,伊娃并没有将自我完全依附于男性身上。“不管她失去的那条腿的命运如何,剩下的那条倒令人印象深刻。那条腿上总是穿着长筒袜、套着鞋,无论什么时间和季节……她从来不穿太长的裙子来遮掩左边的残缺。她的裙子总是到小腿中间,这样,那条引人注目的腿就能为人所见,同时,她左腿下的空当也明明白白。”(34)波依波依的离开,使得伊娃独自面对生活的艰辛和真实的自我。她对身体残缺从不加掩饰,这使得伊娃时刻处于清醒状态并保持鲜明的自我。残缺的身体在一定意义上成了一种符号,它喻示着女性主体性的表达,成为伊娃自我不可或缺的构成。在女儿汉娜烧死自己后,伊娃从此闭门不出,几乎隔绝了与外界的往来。对身体的自我幽禁,这种极端的做法实际上展示出伊娃几乎完全摒弃了个体的社会化方面,进一步强化了自我。
与伊娃的残缺和幽禁状况不同的是,她统治的匹斯女性王国呈现出生机勃勃的面貌,这是伊娃主体性的延伸。在人类历史实践中,人们往往把残疾和幽禁与生命力的逐渐消亡联系起来。然而,这显然不是唯一的答案。伊娃自从波依波依归家又离去后,便不再走出卧室,但正是在这个有限的空间里,伊娃释放了前所未有的自我的可能性。“秀拉·匹斯家有许多房子,都是在过去几年中按照主人的明确要求不断增建的:今天加一条楼梯,明天盖一个房间,东开一座门,西修一条廊。结果有的房间开了三扇门,有的房间又只有朝着门廊的一扇,与房子的其他地方无门相通,而有的房间要想进去只得穿过别人的卧室。”(33)这所奇怪的房子自身充满了流动的欲望和各种可能性。对房子的改造是伊娃主体性表达的一种方式。她把房子进行了非常规改造并把底层租给各式各样的人。在收留的房客中,有几个年龄相差不大的男孩子,伊娃把他们都叫作杜威。一开始大家都能以其个性把孩子分为黄眼杜威、雀斑杜威和墨西哥杜威,后来三个人逐渐成为一体,没人能分清他们。伊娃的做法实际上是对个性的抹杀,对秩序、中心和确切的调侃和嘲弄,使匹斯女性王国成为一个异于男性统治的世界,是一种突出的解域化实践。有评论称,“伊娃是完全自主的典范,她可以自愿做出抉择,她像女神一样建设、统治着她的家庭”[19]。伊娃的自我幽禁和生机勃勃的匹斯王国具有突出的一致性,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后来伊娃被秀拉送进了养老院,她那条生机勃勃的腿就丧失了生命力。
伊娃对其他男性的爱超出了责任和依赖,这更新和强化了她的女性自我。在丈夫再次离开后,伊娃并不拒绝他人的造访并与男性建立了和谐的关系。“尽管伊娃年岁已大,又是独腿,还是有一批男人来造访,她虽然不与谁确立关系,但热衷于调情、亲吻和开怀大笑。男人们愿意瞧她那好看的小腿、整洁的鞋子和深邃眼中偶然滑落的注视。”(45)男人们的这种“看”显然是一种基于平等关系、带有距离感的注视,而非丈夫对作为“附属物”的妻子的“看”。而伊娃也用同样的视角注视男性。没有婚姻关系的束缚,恰为伊娃保持自我提供了客观条件。伊娃对男性的爱单纯而热烈,甚至有些偏袒男性。“她总是小题大做、没完没了地责怪新婚妻子们没有按时给男人把饭做好,教育她们该怎么洗熨和叠衬衫。”(45)伊娃对婚姻中女性的要求实际上是在强调两性关系中女性的责任。伊娃看似站到了其他女性的对立面,成为男性共谋,但结合她个人经历来看,伊娃的做法实际上体现了她对两性关系的深刻认识:女性不是男性的附属品,而是独立的,在两性关系中需要担负起自己的责任,这是对单纯强调权力的激进女权主义的革命性推进。
不可否认,伊娃通过身体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建构了女性自我,然而这种自我始终没有跳出两性的二元结构和社会对女性塑造的窠臼。在秀拉外出多年归来后,伊娃表达了她对秀拉的要求,“你打算什么时候结婚?你该生个孩子了。那样你就可以安心了……可没有哪个女人游手好闲地到处逛,还没有男人”(98)。伊娃把女性和结婚生子联系在一起,并在之前的生活中履行着社会赋予女人的种种角色和义务,它与伊娃的解域化实践形成了相对稳固的关系。后来伊娃被送进养老院,其鲜明的主体性伴随着肉体能力的消退而减弱。
(二)汉娜的自然之性与秩序的破坏
人类对身体功能的认识和处置实际上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变化过程,尤其是进入现代社会后,女性身体被塑造、消费,在很大程度上致使身体走向其自身的反面并部分地造成了身体功能的遮蔽。性作为人类身体的基本生物属性,它被赋予了过多的社会意识形态色彩。考古学发现,女性的性器官在人类早期是被作为神圣之物的,及至现代社会,性被打上了诱惑的、下流的记号。广泛存在于非洲大陆的女性割礼就是要对女性天然的性器官进行改造,使其无法获得快感,从而确保女性对丈夫的忠贞。对性的意识形态化根本上是便于社会管理,男性正是通过性政治来达到对女性的控制。最初的性功能实际上是生物的自然属性,并不具有区别意义,而对性功能的道德化就属于德勒兹讲的层化或界域化,这种界域化摒弃了性的多重可能性,甚至使其忘记了自身的属性。
汉娜首先摒弃了现代社会对身体的装扮,进而完成了对身体自然属性的回归。巴特勒在其著作《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中提出了性别的操演性建构,认为装扮是对性别的模仿。[20]在其理论观照下,装扮的意义被放大。青少年中颇为流行的 cosplay 即是一种装扮,装扮者通过服饰、妆容、造型的改变企图获得动漫形象或历史人物的某种特征或属性,以此寻求一种异于日常存在的心理感受。与此相似,流行于西方的新部落主义,失业青年通过文身、刺青、佩戴面具等方式寻求一种原始部落文化带来的心理体验,以此来抵御残酷现实对个体的压迫。与以上操演行为相反,汉娜所做的是把现代社会对身体的种种消费、规训、改造的痕迹一一去除,还原身体的自然属性。“她从来不会去梳一下头发,赶忙换套衣服或是飞快地化个妆,她不扭捏作态,而是用性吸引力在男人心中投下涟漪。”(46)汉娜的操演是要摒弃附加于身体上的种种“物”的价值,进而还原或放大来自身体自身的能量。
汉娜集中演绎了女性躯体的自然之美和原始的性吸引力。汉娜在丈夫死后,带着三岁的秀拉回到了母亲家。在这个女性之家,汉娜和伊娃一样,保持着与男性的正常交往。汉娜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天然和真实。“夏天,她总是光着脚穿条旧连衣裙,冬天则趿拉着一双后帮被踩平的男士皮便鞋。她让男人们注意到她的臀部、她纤细的足踝、她那露水般光滑的皮肤和长得出奇的脖子,还有她那含笑的眼睛、她转头的模样——一切都这么来者不拒、轻松而讨喜。她说话时声音拖拽着慢慢下降;哪怕最简单的字眼,在她嘴里都会发出最和谐的音调……无论哪个男人听见后都会把帽子往下轻轻一拉扣过眼睛,往上提提裤子,同时想着她颈根下的那处凹陷。”(46)这段关于汉娜的臀、踝、颈、眼等身体及与身体相关动作的描述完全是一曲身体的赞歌,传递出女性躯体之美。尽管这种“看”或者“注视”多少带有男性欲望和男性塑造的痕迹,但汉娜的身体及其释放出来的原始性吸引力无疑成为其主体构成中非常突出的部分,使人感受到自然和原始的力量,这与作为消费的身体所制造的诱惑迥然不同。
汉娜随意的性行为是对现代社会伦理秩序的挑战。在三代女性中,叙述给予汉娜的分量是最小的,但她在女性主体建构的历史中却是极为重要的一个人物。与身体紧密关联的是性功能,而性功能在人类历史上被不断地言说,成为权力角逐的一个场域。“文明本身限制性生活的倾向与扩展文化单位的其他文明倾向同样明显。它最初的图腾阶段已经带有反对乱伦性质的选择性对象的限制,或许这就是人的性生活所经历过的最为激烈的转变……由于惧怕被压制因素的反抗,它被迫采取更为严格的预防措施。在这样一个发展阶段,我们西方欧洲文明已经达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准。”[21]家庭关系的缔结本就是人类文明的突出表征,它具有重要的社会管理使命。历史上,家庭内部的性行为是被社会认可的,此外的性行为则被认为是不道德的。汉娜的行为则打破了这种秩序和道德原则而且丝毫不以此为耻,“她可以在一个下午和新郎上过床,又去为新娘洗碗”(48)。同时,汉娜对情人的选择是基于自然的性吸引力,其行为只是满足自己的需要,从不对性对象提出情感要求。这就使得汉娜在男人中间具有极好的印象,但同时激怒了镇上的女人。“汉娜在跟谁睡觉这一点上偏偏是很挑剔的……跟人睡觉对她来说则意味着一种对信任的衡量手段和确凿的承诺。”(47)汉娜对与男性建立关系有着一种超然的自觉,她不愿卷入任何一个确定的关系中,保持了自我的独立性,将社会利用性功能进行管理的模式抛弃于日常之外。
汉娜对两性关系的认识和实践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她恢复了人的原初的自然属性,把现代社会对身体的改造和规训,以及历史上通过性政治来实现社会管理的做法统统抛弃,实现了女性的彻底解放。这种解放使汉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和自主性。跟伊娃比起来,汉娜的身体实践更具革命性,她挑战的是整个社会秩序,其身体实践进入了一个更宏大的女性解放的场域。她的解域化实践所面对的层化空间就是社会对女性的规约,包括控制了人类历史数千年的伦理道德观念。汉娜以自己的身体实践和性的绝对解放完成了自己对以往秩序的解域和逃逸,最终获得了一种异乎寻常的自我。
但值得注意的是,汉娜的自我缺乏明确稳定的意义核心。按照拉康的理论,自我的建立首先是以母亲为对象的,孩童通过母亲的形象来区别自我和他者,这是自我构建过程中的必然阶段。汉娜生活在一个男性缺失的家庭中,先是父亲在他们儿时离家出走,成年后丈夫又早早去世。对汉娜来说,母亲是其意义感的来源,但儿时的一度缺席和此后多年的淡漠里,汉娜对来自母亲的情感始终存有疑虑。当汉娜的弟弟李子在战争归来后一蹶不振并开始吸食海洛因时,伊娃发现儿子被摧毁后亲手烧死了他。汉娜对此十分困惑,专门去询问伊娃:“我是说,你有没有爱过我们?你知道,在我们还小的时候。”(72)伊娃肯定的答复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汉娜的疑虑,但她的生命中始终缺乏某种核心要素,致使汉娜的形象具有些许轻盈漂浮的特质。
(三)秀拉“漂泊”的身体及与孤独的对抗
“漂泊感”是后现代社会的一种普遍的生命体验。从萨特的《恶心》到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和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西方现代文学无不传递出现代人精神的荒芜和漂泊。漂泊是对固定和中心的对抗,是西方社会对二元对立的稳固结构的一种反驳。莫里森作为一名少数族裔作家,她以自己的切身体会和鲜明立场展开了对美国黑人生活的书写,但不可忽视的是,《秀拉》异常突出地涉及了现代社会中普遍的议题:孤独。这显然超越了以种族为核心的叙事,使作品更具普遍意义。作家曾在一次访谈中表达了她对拉美文学的赞赏,直言不讳其对自己文学创作的影响。[22]我们在《秀拉》中可以或多或少地感受到《百年孤独》的审美品格,同名主人公对孤独的体味和理解异常深刻。
奈尔和秀拉儿时互为镜像的关系强化了主人公“自我”的追求。小说中,奈尔是较早出场的一个人物,被母亲培养得非常乖顺,但在一次南部之旅后自我开始觉醒。“我就是我。我不是他们的女儿。我是奈尔。我就是我。我。每次她说到‘我’这个字眼,浑身就聚集起一种东西,像力量,像欢乐,也像恐惧。”“这次旅行,抑或她所发现的那个‘我’,给了她无视母亲的阻拦去交一个朋友的力量。”(31)奈尔的“我”是在被母亲控制的生活的裂隙中获得更新的自我,她看了母亲不经意间对白人列车员露出谄媚和挑逗笑容时黑人军人的煎熬表情,这促使奈尔坚定地开启了“自我”之旅。为了标榜和凸显自我,奈尔冲破母亲的偏见发展自己的友谊,开始与做了五年同学而没有任何交往的秀拉做朋友。奈尔母亲阻挠的原因是秀拉母亲汉娜“黑得像煤烟”以及她的懒散,这是浅肤色黑人对深肤色黑人的惯常看法。在伊娃和汉娜的影响下,秀拉性格自由而独立,她与奈尔的交往更是强化了彼此的个性。“在为彼此营造出的安全港中,她们对别人的做法不屑一顾,专心于她们自己感受到的事物。”(58)
秀拉最早的身体实践是童年时期为了保护奈尔对自己实施的身体暴力。奈尔经常遭到白人学生的欺辱,秀拉在数次忍耐后选择直面对方并采取行动。她拿出伊娃的水果刀并在一群白人学生面前割破了自己的手指。“四个男孩目瞪口呆地望着那伤口和像朵小蘑菇那样卷曲着的豁开的肉,殷红的血一直流到石板的边缘。”(58)在两性的较量中,大部分女性力量较弱,无力施暴于男性,转而把愤怒和暴力施加于他物或者自身。与伊娃相似,秀拉试图通过伤害自己的身体以达到对对方的威慑。在这个过程中,秀拉对自己身体的处置显示出一种积极的姿态,这也是一个黑人女孩对抗包括白人男性在内的“他者”所采取的初步行动。受秀拉的影响,奈尔有意识地释放了自己被压抑的天性,不再毫无意识地跟随母亲的意志,放弃了对“高鼻梁”、“直发”的执着,对身体表现出强烈的放任姿态。但是,这次暴力事件也是二人日后分道扬镳的暗示。奈尔对于秀拉的果敢表现出了极大的诧异,“她一直盯着秀拉的脸,它似乎有几千里远”(58)。奈尔的反应显示了二人在思想上的距离,秀拉以实际行动捍卫自我,而奈尔则在前者或二人共同营造的更为宽松氛围中追求和表达自我,是一个追随者的形象。后来,奈尔的婚姻和秀拉的离去使奈尔曾经觉醒的“自我”淹没在庸常的黑人妇女生活中,逐渐进入与秀拉相对的“大多数”队伍当中。
与汉娜对性的依赖不同,秀拉利用性、把性作为排解孤独的手段,身体的解域化实践更为彻底和深刻。在伊娃和汉娜的影响下,秀拉认为性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因而并不排斥,也没有社群中普遍存在的道德感。但不同的是,伊娃和汉娜的解域化实践是建立在对男女两性认可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她们尽管借助自己的身体实践反抗男权社会,但始终没有跳出二元对立的窠臼。秀拉的性实践,则是一种去中心化的实践,是对传统二元对立的消解。小说中穿插了一个有趣的叙述,即对裘德急于结婚的原因的叙述。裘德本不想结婚,意欲在社会建设中大显身手,但当地的修路工程把所有的工作机会留给了白人,而他只能到酒店当侍者。“没有她,他不过是个女人般围着厨房转的侍者。有了她,他就是一家之主。”(88)裘德并非是出于爱,而是迫切地需要一个女人来树立他的男性尊严和统治地位。通过奈尔和裘德的婚姻,小说揭示出社会对两性的塑造和男权的生产机制。秀拉在十年后返回梅德林,与裘德的性关系破坏了她与奈尔的友谊。在秀拉弥留之际,奈尔质问秀拉,秀拉回答:“好吧,在我前面,在我后面,在我脑袋里,有块空地。某块空地。裘德填满了这块空地。就是这么回事,他只是填满了这块空地。”(156)在秀拉看来,裘德抑或其他男性的存在都只是工具,是服务于秀拉的孤独和不完满的自我的。当她试图与阿贾克斯保持稳固的恋情时,对方一如小说中的其他男性,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离开。可以说,这是秀拉的一次失败的情感经历,固定关系导致了对方的逃离。“秀拉的情感本质上反映了她的开放性和流动性。”[23]因此,秀拉随意的、放任的性实践驱逐了它与社会之间的稳固的意义指向,进而确立了一个新的所指。冠以孤独之名的所指并非是一个实体,这就形成了一种流动与漂泊之感。
小说中作为秀拉“漂泊”或“去中心化”身体的表征和突出意象的是她额头的胎记。“秀拉的皮肤是深棕色的,长着一对沉静的大眼睛,其中一只的眼皮有一块胎记,形状如一朵带枝的玫瑰。这块胎记为本来平淡无奇的面孔增添了一丝破碎的灵气和一种刀光般的戾气。”(56)胎记本身是身体的一部分,完全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特征和属性。然而,在人类的身体史中,人们往往会把这种自然属性与人的行为本身联系起来,进而认为胎记是异常的,是邪恶的征兆。在小说中,秀拉额头的胎记在其人生不同阶段和不同人眼中被做了不同解释。叙述者说这是一支带枝的玫瑰,退伍士兵夏德拉克认为“她的眼睛上有一条蝌蚪”(169);当秀拉在1937年回来时,裘德则认为她额上的胎记是一块铜斑蛇。“裘德看着妻子的这位朋友,心头微微燃起怒火,这个苗条的女人姿色不算平庸,但眼帘上有一块铜斑蛇那般的胎记,也不算多好看。”(111)在秀拉把裘德弄到手并使他离开了奈尔,同时把伊娃送到了养老院后,梅德林镇上的女人改变了对秀拉的看法。“那不是一株带枝的玫瑰,也不是一条毒蛇,而是从一开始就给她做了标记的汉娜的骨灰。”(124)镇子上的人开始以最恶毒的方式评判秀拉的胎记,把她作为道德的反面,所有的人都尽力做好自己的事情以拉开与秀拉在道德上的距离。有评论认为:“她的性生活方式和自我掌控造成了她与城镇里居民疏远。”[24]秀拉的特立独行使其成为镇子黑人居民遭受政治挤压的“替罪羊”,就像《天堂》中修道院的女人,为镇子的道德堕落背负起了恶名。胎记成了异端的身体表征,而这种变化不定的形状是秀拉去中心化身体的表征。
情感的匮乏和信仰的缺失是秀拉“漂泊”或“无中心”自我形成的原因。与汉娜相似,导致秀拉“漂泊”的是情感上的疏离。作家意在写黑人女性的独立和人类的孤独,并不因此否定感情的意义。秀拉在童年曾无意间听到母亲与他人的聊天内容,汉娜表达了对秀拉的爱,同时表示自己不喜欢这个女儿。对秀拉来说,亲情是构成她坚实、固定自我的基础,而祖母烧死李子、汉娜的放纵都挑战了秀拉的底线并对其自我建构产生影响。“她的生活是一种实验——自从母亲的那番话让她飞快跑上楼梯,自从她的责任感在那片河岸上随着河中心消失的漩涡一并消逝。前一次经历让她明白世上没有其他人可以指望,后一次则使她相信连自己也靠不住。她没有一个中心,也没有一个支点可以让她围绕其生长。”(128)
埃利奥特·提伯在《制造伍德斯托克》中塑造了一个同样孤独的形象。与提伯相似的、备受西方传统文化及现代社会压抑的年轻人自发地集结在1969年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掀起了一场以音乐为主的反文化运动。他们通过摇滚、性放纵、反越战等活动充分地彰显了对社会的对抗和对自由的追求。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风起云涌的各类运动持续地把这种精神推向高潮。有趣的是,秀拉尽管脱胎于传统黑人女性群体,但其形象更多地带有这个时代青年的影子,并不像包括《最蓝的眼睛》《宠儿》等作品在内的莫里森其他小说中的女性。有评论称秀拉是典型的“美国存在主义者”[25],此言不虚。秀拉身上的革命和叛逆气质代表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青年的精神状态,具有突出的普遍性。小说里与秀拉在精神气质上相同的人包括退伍黑人夏德拉克。夏德拉克从一战战场归来就处于一种疯癫的状态并在梅德林创立“全国自杀日”。“自杀日”的创立实际上是直面和挑战人类终极恐惧的做法,夏德拉克通过这种做法缓解战争带来的后遗症。夏德拉克的疯癫中不乏对生活真谛的认识。童年的秀拉无意间把名叫“小鸡”的黑人孩子甩进河中,夏德拉克刚巧看到。秀拉因为恐惧而造访形单影只的夏德拉克,他用一句“一直”向秀拉做出了永恒的许诺。与秀拉的这次“联系”成为夏德拉克孤独生命中的阳光,以至于在秀拉死后,夏德拉克一度进入茫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