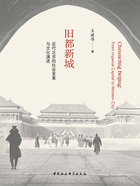
一 管理体制变革
国都作为王朝政治中心所在地,是一种特殊的城市形态,管理模式往往与一般地区不同。明清以来,北京作为国家政治中枢,主要由政治因素统领,整座城以皇城为中心,为皇权政治服务是首要职能,功能单一。尤其是清代建都北京之后,实行旗民分治,皇城之内,直属中央内务府统一管理。皇城之外,分别按照满、蒙、汉八旗方位,驻军防守。在形式上,北京并不存在一个专门的独立性行政管理组织,城市内部的各项事务分散在中央政府、顺天府以及下辖的大兴、宛平两县,两县以中轴线为界,分别管理东、西城区及近郊地方行政事务。总体而言,中央政府与地方机构共同管理城市。步军统领衙门、五城兵马司与顺天府共同负责京师地区的治安、诉讼、赈恤、道路沟渠治理等事项。国都地位尊崇,各个机构层级复杂,关系盘根错节,需要建立特殊的行政管理体系,一个纯粹意义上的地方性机构无法有效承担城市管理的全部职能。
国家肌体机能的逐渐衰弱导致国家控制能力的持续下降,在国都的主要表现之一就是治理水平的下降。清代后期,皇权专制能力逐渐下降,加之“经费不裕”,“事权不一”,京师之地原有的多头管理体制“积久生弊,渐皆废弛”,城市环境恶化。[1]1900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国都沦陷,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原有的城市管理体系遭到严重破坏。联军退出,清廷开始实行“新政”,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推行全面改革。北京作为政治中心,“近接政府则教令易施”[2],受此影响最为直接而明显,以此为契机,开启了自身的城市化进程。
城市的开放与功能转型催生了与之相应的治理与维护机制。中央政府西逃,京城原有的行政管理体系基本解体,形成了暂时的权力真空,社会秩序陷入混乱,八国联军对北京实行划定管界,分区占领,打破了内城原有的行政管理体系与建制。为了确保北京的正常运转,维持地方治安,清廷留守官员与各国占领军协商,由各占领区的士绅出面,组成临时治安机构。当时名称不一,此处统称为“安民公所”,主要职责是协助各占领国对城市各占领区实施管理,覆盖了人口管理、公共卫生、社会治安等多个方面,“原因洋兵初入京城,维时官权未便显露,故以绅士联络洋人,以地方联络绅士,一切紧要事件呈明五城酌核办理”[3]。安民公所存在时间很短,随着各国撤离北京而解散,但其对北京城实行分区划定管界,改变了原有的八旗与五城分区格局,并动摇了里甲制度这一封建行政根基,打破了清代以来一直延续的北京内城行政建制。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之后,清廷逐渐恢复对北京内城的统治权,但庚子中联军对于城市的一些治理经验也延续下来。根据当时城内各民族、各阶层混居,百业杂处的实际情况,原有的依托于八旗体制下的城市管理模式已经不再适用。因此,在奕诓等人建议下,仿照西方城市警政制度,在安民公所基础上设立善后协巡总局,主要维护京师地区的社会治安,几乎不涉及城市建设和公共管理等事务。总局下设各分局,分驻内城和皇城,实行分区段驻守巡逻,基本沿袭了安民公所的区划。此为北京建立现代警政制度的雏形。
城市的开放和功能的近代化要求与之相应的管理与维护机制。庚子之乱对北京造成的冲击逐渐弱化,京师社会局势逐渐企稳。鉴于善后协巡总局的过渡性质,清政府于1902年筹办工巡总局,替代了善后协巡总局。工巡总局分为内城工巡局与外城工巡局,除保留善后协巡总局原有的维护治安的职能外,增加了城市建设与管理的职能,包括市政工程、交通管理、公共卫生、社会救济等方面。工巡总局仍以治安为首要任务,城市建设与管理只是其附属职能,还处于初级水平。但这一机构已经初步具备了近代市政管理机关的基本特征,为北京城市化进程奠定了初步的行政基础。
1905年10月,清政府接受袁世凯的奏议,设立巡警部。巡警部成立之后,立即开始接收工巡总局,将其改组为“内外城巡警总厅”,隶属于巡警部,这也是中国最早的真正具备近代意义的城市警察机构。内外城巡警总厅设内城分厅五,外城分厅四,各分厅以下,更分内城二十六区,外城二十区,区置区长、副区长各一人。内外城巡警总厅职能涉及范围广泛,不仅负责管理京师内外城一切警务,而且还覆盖北京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建设与公共事务的管理等,包括社会治安、人口普查、市政、交通、消防、公共卫生、社会救济、工商业管理等,分官设职,各尽其能,各司其责。1906年,清政府厘定官制,建立民政部,撤销巡警部,内外城巡警总厅也改隶民政部。徐世昌为民政部尚书,“奏派巡警总厅两厅丞,内城为裁缺鸿胪寺少卿荣勋,外城为候选道朱启钤,此为创设京师市政之始”[4]。内外城巡警总厅的机构与职能经过调整之后,作为城市管理机构的角色进一步明确。[5]
作为清末“新政”的一项措施,1909年,清政府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与《京师市自治章程》,前者在中国历史上首次以法律形式确认了城、乡分治的行政管理理念以及城市的法律地位,是近代城市化的里程碑,城乡从此有了不同的行政系统;后者则标志着北京城开始由国家的附庸向具有自治意义、独立法人意义的城市转变。[6]与此同时,清末还相应颁布施行了一系列北京城市管理法规,北京日益凸显其成为一座近代城市的基本特征。[7]
民国建立之后,内外城巡警总厅于1913年改组为京师警察厅,隶属于北京中央政府内务部,继续行使原有的各项城市管理职能。改组后的京师警察厅内添设消防、督查二处,合旧有总务、行政、司法、卫生四处,共为六处,下辖内城十区,外城十区,职能涵盖社会治安、人口普查、税收、赈济、公共卫生等。由于帝制瓦解之后,此时紫禁城及皇城的最终命运还未可知,京师警察厅将前清时期中央各部负责的大部分管理北京内城的工作承接了下来,成为一个职能明确、独立性较强的一级城市行政机构。此后一直至1924年之前,京师警察厅统辖北京内外城共二十区。
1914年10月,北京市政府颁布《京兆尹官制》,规定顺天府改名“京兆”,设立京兆特别行政区,直属中央。京兆特别行政区主要负责北京城周边区域事务,对于城区内部(内城与外城)事务基本不插手。这样一种治理体系标志着北京传统的城乡一体的地方治理模式已经被打破。
随着北京城市化进程的加速,由警察机构统揽城市公共事务的体制已经不能适应近现代都市建设的要求。1914年8月,在内务总长朱启钤的极力推动下,北京政府设立京都市政公所,“办理京都市政”,职员多为兼职,历任督办多由北京政府内务总长或次长兼任。[8]作为一个专门性的市政机构,京都市政公所“成立之初,市政草创,措施极简。惟于开放旧京宫苑为公园游览之区,兴建道路,修整城垣等,不顾当时物议,毅然为之。且于规定市经费来源,测绘市区,改良卫生,提倡产业等,均有所倡导”[9]。这一机构的建立对于北京近代城市建设的起步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朱启钤也成为北京近代市政的创始者。
京都市政公所建立之后,承接了京师警察厅原有的一些职能,这是北京城市管理体制的一个重要变化。1918年1月,北京定名为“京都”市,市政公所开始“改制设官”,“始具市府之雏形”。[10]“从城市地名演变过程来看,京都市是京师向北平特别市的过渡状态,也是从非建制城市向建制城市过渡的阶段。”[11]1921年设评议会,延聘士绅三十人为评议员。当时市政公所职员分专任与兼职,其中多受过高等教育,一些人还有国外留学背景。这些“技术官僚”对北京城市建设的规划值得重视。此后一直到1928年,北京城的主要事务一直由京都市政公所与京师警察厅两个机构共同负责。二者均向内务部负责,彼此独立,互有分工,但也并非界限严格分明,在一些管理事务上也需互相协作,任职的行政长官有时也有交叉。市政公所负责城市规划、基础设施建设与修缮、经费筹措、卫生行政等;京师警察厅集中负责社会治安、捐税征收、户政、消防、商业管理等,对于二者的职能以及关系,市政学专家白敦庸如此概括:
市政公所历年组织皆偏重于工务,此观于其科或处之职掌可知也。盖市政公所之外,有与其平行之京师警察厅之存在。而警察厅之历史悠久,权力广大,虽号为“管理京师市内警察、卫生、消防事项”,实兼握征收捐税及办理社会事业之权……故十余年来,市政公所之事业,皆囿于工程方面,为内务部及警察厅所划割而出者。至于道路交通,教育补助,慈善救济,公共卫生各事项,不过兼及,并非主要政务。予尝称京都市政公所为京都市工务局,纯出于客观的态度,良以其行政范围狭小,故尔云然。[12]
1921年7月,中央政府颁布《市自治制》规定,京都市市长由内务部遴选,经由国务总理呈请大总统任命。随后推出《市自治施行细则》,规定市分为特别市和普通市两类。自1922年9月1日起,京都市被定为特别市,裁撤以前所设市政督办等职。在自治机关未成立前,暂由内务总长兼理。这是中央政府颁布的第一个关于“市”建制的正式文件,标志着中国“市”建制的发端。
京都市政公所与京师警察厅的管理范围主要限于北京内外城,而城墙之外的四郊地区,也属双重管理体制,步军统领衙门负责治安,大兴、宛平两县负责田赋、教育等项事务。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之后,北京的行政区划又发生了一次明显变动,隶属中央的步军统领衙门被裁撤,京师警察厅接管四郊,划分东、西、南、北郊为四区,各置警察署。至1928年,京师警察厅改组为北平市政府公安局,警察管辖区即成为北平特别市辖区。同时,京都市政公所下属的工巡捐局在1925年分设内外城市政捐局和四郊市政捐局,管辖范围与警厅辖区相同。[13]
1928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所属国民革命军进驻北京,北京政府命运终结。6月20日,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一四五次会议议决,改直隶为河北省,旧京兆区及各县并入河北省,北京改为北平,任命何其巩为北平特别市第一任市长。北平特别市政府随即成立,下设财政、土地、社会、公安、卫生、教育、公务、公用八局,取消了京都市政公所、京师警察厅以及专门管理教育的京师学务局,相关职能被划并到北平特别市市政府下设的各局,“市行政始告完整”[14]。北平特别市成为统辖全市各项行政事务的一级综合性政权机构,它的设置是北京历史上具有时代标志意义的里程碑事件。
1928年7月3日,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国民政府市政法规》,正式规定市分“特别市”与“市”两种,特许建立的特别市为:中华民国首都、人口百万以上之都市、其他有特殊情形之都市。同日颁布的《特别市组织法》规定,特别市直辖于国民政府,不入省县行政范围。特别市政府在不抵触中央法令范围内办理:1.市财政事项。2.市公产之管理及处分事项。3.市土地事项。4.市农工商业之调查、统计、奖励、取缔事项。5.市劳动行政事项。6.市公益慈善事项。7.市街道、沟渠、堤岸、桥梁建筑及其他土木工程事项。8.市内公私建筑之取缔事项。9.市河道、港务及船政管理事项。10.市交通、电气、电话、自来水、煤气及其他公用事业之经营、取缔事项。11.市公安、消防及户口统计等事项。12.市公共卫生及医院、菜市、屠宰场、公共娱乐场所之设置、取缔等事项。13.市教育、文化、风纪事项。[15]
北京虽失去国都身份,政治地位一落千丈,但其行政管理却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由于被国民政府列为直辖于中央的“特别市”,北平摆脱了过去将城市管理分成若干区域,分属不同机构负责的传统治理模式,成为由市政府统一管理的现代城市型行政区。根据《特别市组织法》,北平市政府设立市政会议,由市长、秘书长、参事、各局局长组成,并根据会议内容指定某些科长、股长等有关人员列席。市政会议制定了诸多法律、条令以及实施细则,内容涵盖了城市管理的各个方面。市政会议使北京城市管理走上了法规化、制度化的轨道。
北平特别市政府的建立虽属城市管理体制的重大变革,但建立之初,各项制度尚在探索试验阶段,未入正轨。同时,这一时期市长屡次易人,经历张荫梧、胡若愚、周大文、王韬等任,市政府各项事务进展艰难。1930年5月,国民政府又颁布《市组织法》,废除了特别市和普通市的划分,将全国城市划分为院辖市和省辖市。同年6月,北平一度改归河北省辖,“特别市”名称不再,河北省政府也由天津迁至北平。但仅几个月之后,北平市再改为行政院管辖,河北省政府又移归天津。[16]北平市政府内部的各局也在不断归并或裁撤,1932年,原有八局重新调整为社会、公安、工务三局,而且各自规模也发生紧缩。
1933年,袁良出任北平市市长,在市级行政管理体制上健全组织,首先恢复财政、卫生两局,将教育、公用并入社会局,地政并入财政局,连同原有的公安、工务,共五个局。袁良任内也是民国时期北平市政建设的一个重要时期,“各项设施,渐入正轨,财政较前充裕,债务渐次偿还,民生设施,职员考核,大见进步,尤以创办公共汽车,实施文物整理工程,修建道路,力倡卫生事业,最足称道,实为北平市政建设之黄金时代”。1935年之后,日军侵入华北腹地,华北危机日益严重。袁良卸任市长之职,秦德纯继任。“当局苦于支撑残局,在市政方面,完全萧规曹随,无为而治:幸袁任内创办之事业,如市行政制度之奠定,市财政收入之增加,道路建筑卫生之建设等,已大见功效,继任者坐享其成。”[17]
从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北平经历了日伪北京特别市统治时期。日军侵占北平之后,以此为基地,以“建设华北人的华北”为旗帜,采取“以华制华”方式,网罗亲日派,在短时期内初步建立起一套统治华北的殖民体系。1937年8月1日,在日本驻北平使馆陆军助理武官今井武夫等人的操纵下,推出了由北洋遗老江朝宗担任会长的“北平地方维待会”。8月18日,“维持会”以常务会议的名义,推举江朝宗任北平市市长,从此北平市政府与“维持会”合为一体。1937年10月12日,“维持会”改北平为北京。12月17日,“维持会”宣告结束使命。1938年1月1日,北京市政府改称北京特别市政府,1月13日又改称北京特别市公署,余晋龢任伪市长,改组市政府组织,在原社会、财政、工务、卫生、警察五局之外,另增设教育局与公用管理总局,共为七局。自此,一套完整的日伪殖民统治机构在北平正式运转。
1937年12月13日,中华民国首都南京陷落。12月14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平中南海居仁堂成立,在其宣言中指责国民党“构衅邻邦,同种相噬”,以承继北京政府法统为标榜,沿用中华民国年号,定都北京,声称取代国民党中央,建立“全国性”政权,王克敏出任政府行政委员长。成立初期,只下辖北平和天津地区,随着战争深入,管辖范围逐渐扩大至河北、河南、山东和山西部分地区以及青岛特别市。
日军在北平一方面扶植傀儡政权,同时仿照伪满洲国“协和会”的形式,组建“中华民国新民会”(简称“新民会”)。1937年12月24日,日伪北平“新民会”宣告成立,它号称是与“政府表里一体”的“纯正民意机关”,其纲领为:“护持新政权,以图畅达民意;开发产业,以安民生;发扬东方文化道德;于剿共灭党旗帜下参加反共战线;促进友邦缔盟之实现,以贡献人类之和平。”[18]“新民会”实际上是侵华日军为控制占领区民众而创建的殖民组织,其机构设置与政府行政机构相平行,重要职位都由日本人担任。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之后,南京中央政府任命熊斌为北平市市长。10月,重建北平市政府,设社会、财政、工务、卫生、教育、公用、警察、地政八局,市长以外设副市长一人,市府设秘书、总务、人事、会计、外事五处,参事、技术、专员、统计、会计、视察、编审七室,组织庞大,行政费用增加。北平沦陷已有八年之久,百废待兴,财政紧张。1946年11月,何思源担任市长,开始调整组织,裁汰冗员,紧缩财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