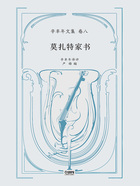5.窃记秘本合唱曲
你常听人说起罗马那首出了名的《求主怜悯歌》。此曲是如此之珍贵,凡是去西斯廷教堂参加演唱的人,连一份分谱也不准带出堂外抄写,不管是自己用还是传给他人;否则,便要受到革出教门的严厉处分。
可是,我们现在已经弄到了这个曲谱。沃尔夫冈把它默记下来了。假如不是因为在我们萨尔茨堡无须演唱此作的话,那么此刻便可随此信寄出了。
其实,此曲演唱效果之所以特殊,是由于那演唱方式比乐曲本身更起作用。因此,我们将把它随身带回家去。更重要的问题是,此谱在罗马这里是一种珍秘之物,我们不想让其落入他人之手,免得因此而遭到教廷方面的处罚。
——老莫扎特1770年4月14日自罗马寄妻子
译读者言:少年莫扎特凭着他过人的听力与记忆力,窃记了那首从来秘不外传的《求主怜悯歌》的乐谱,打破了教廷的禁锢,这是乐史中一件大掌故!
虽然可惜缺少当事人莫扎特本人对这事的叙述,然而有乃父的家信,还有他姐姐的回忆。且说南内尔1792年的回忆是这样的:
“一到复活节前的星期三下午,他们父子两个立即赶往西斯廷教堂,去听那首出名的《求主怜悯歌》。由于向来的规矩是此谱不得外传,儿子便承担了将其听记下来的工作。结果是他一回到寓所中就动手默写出来。次日,他又去听了。他把已经记下的谱子藏在自己帽子里头,为的是对一下有无误记之处。不巧,那日演唱的作品换了一首。等到耶稣受难日(星期五)那天,才终于又听了一遍。回来之后,订正了几处,便完成了。
这件事随后还是在罗马传开去了。于是,他在音乐会中在羽管键琴的伴奏下唱了它。”
当时的家信与后来的回忆,两份乐史文献为这件曾被视为神奇不可思议的异闻作了颇有现场感的报导。但是我们还可以来作一些有趣的补充,使其更加接近于历史之真。
首先,从前广为流传,并见诸各种记载的说法是,十四岁的莫扎特仅仅去西斯廷教堂听了一遍,便将那共有九个声部的复调作品一无差错地暗记于心,默写出来了。
经过乐史家仔细查证,现今已将“一遍”修正为“两遍”。南内尔的回忆即最有权威的见证了。更可贵的是,她提到了第一回听记之中有些不准确之处,而且莫扎特本人也不认为自己的听、记是万无一失的。这就把神话色彩和广告气味给洗清了。(令人不解的是1980年出版的《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词典》中关于“莫扎特”这一条目中,那说法依旧是只听了“一遍”!)
不过,进一步考证,又仍有叫人纳闷与猜疑的情况。有人对其父其姊的说法提出了疑问。问题的“要害”在于:莫扎特在这以前真的是从未听见过这首《求主怜悯歌》吗?
据考,当时在罗马以外的有些地方,其实是可以听到这首作品的。它在维也纳便曾经被演唱过,不过那时莫扎特还很小。至于曲谱,西斯廷教堂之外也不是没有抄本。奥地利皇帝利奥波德一世,葡萄牙国王,还有那位年高望重、同莫扎特颇有缘分的玛蒂尼长老,他们手里都有一份此谱的抄本。
就在莫扎特听记此曲的那年,即1770年之前,英国的乐学家伯尔尼已经了解到这些情况了。而玛蒂尼长老正好在莫扎特赴罗马之前三星期曾经给他上了对位法课。他并不是没有机会听到它和见到那乐谱。那么,老父的报导是否不免有点故神其说?
其实就是《求主怜悯歌》本身也有其名不副实的成分。原作本是五个声部的合唱曲,后来唱成了九个声部。另外的四个声部是后加上去的,这是一种按着中世纪配和声复调的成规由演唱者加在曲调上的唱法。老莫扎特家信中的“演唱方式”云云,说的正是这情况。
以往,普通的爱乐者虽然都神往于这个莫扎特神话中极具吸引力的故事,但恐怕极少有人能有见识一下这首古老且又保了密的音乐文献吧?除非你有机会在天主教复活节的时候到罗马西斯廷教堂去。
如今却太容易了。你可以从CD上一赏这乐中珍奇。很可能,乐曲本身并不像你原先想象中那么神奇美妙,但它是古意盎然的。尤其不同凡响的是,它是沾了莫扎特的灵光的。它会把你一下子带回二百多年前去,让你与绝世天才同在。这是一种为史感所强化又升华了的乐感。作曲者比听记者又要古二百年。他是阿来格里(G.Allegri,1582—1652)。
也像是一种历史的嘲弄,写了大量教堂音乐作品的这位乐人,后人和今人却只记得他这部《求主怜悯歌》,然而这号称九声部的乐曲,又只有五个声部是其原作;而那演唱效果,又主要是由于外加的那些声部。所以,他的版权实在是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