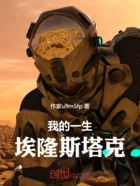
第6章 核子时代(1945)
人类文明之钟拨回到一个世纪前。
1945年,美国,新墨西哥州。
阿拉莫戈多沙漠的黎明泛着铁青色,那遥远而辽阔的荒漠之中,天空一碧如洗般的湛蓝,无垠的沙地延伸至视线的尽头。在这个看似普通的清晨,空气里却弥漫着一种不同寻常的紧张与期待,仿佛整个大自然也在屏息以待。
罗伯特·奥本海默用冻僵的手指第三次调整着望远镜焦距。他划亮火柴,火苗在烟卷末端明灭的瞬间。
四年前,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加入同盟国,正式对德宣战。与此同时,他被任命为“曼哈顿计划”总工程师,设计制造世界上第一个原子弹。
四年的时间里,在这片广袤的沙漠腹地,一座完整的小城市拔地而起,里面汇聚了全世界1000多名最优秀的科学家和和3000多名军事人员,他们都在为同一目标而昼夜奋斗。现在,到了项目最后验收的时刻。
“芝加哥1号堆临界那晚,你也是这副表情,就像梵蒂冈主教发现上帝在玩骰子。“
不远处,核反应堆之父恩利克·费米将深色三件套西装脱在了一边,露出其卡其色羊毛背心和条纹棉质衬衫内搭,然后用解放出来的手臂把碎纸片抛向空中,并观察纸片的轨迹。
这位物理学家在计算冲击波当量时总是喜欢用触感辅助。当数到第七张碎纸片时,沙漠的风突然停了。他将报纸裁成的方片举过头顶,布料下的皮肤还残留着三年前芝加哥实验室的辐射灼痕。
“风速每秒12米,“费米用母语自语,他卷起衬衫袖子,漏出的手臂有道闪电状的疤痕,那是罗马大学粒子加速器事故的纪念品。
“亲爱的恩利克,“奥本海默看着费米认真的样子,指着远处的一顿探测设备调侃道,“要不要赌一赌你的纸片法和那堆探测器谁更准?“
“好,就赌你藏在保险柜的雪利酒,冲击波到达时间不会超过40秒。“费米从背心口袋掏出镀金怀表,表面法西斯束棒徽章在晨光中泛冷,表盖内侧用镭涂料写着芝加哥的经纬度,是妻子劳拉缝制的辐射计量器。
不远处的曼哈顿计划总指挥格罗夫斯将军沉默地叼着雪茄,雪茄烟灰落在大理石纹记事本上,烫穿了记载着十二亿美元预算的纸张。
他没有理会手下两位爱将为缓解紧张而下的赌注,而是定定看看着远处地平线上那座30米高的铁塔——
此刻,它正孤独的矗立在那里,八根钢索从塔顶辐射状垂下,吊着一个浑圆如中世纪瘟疫医生的青铜装置,就像倒置的保龄球。
晨风掠过钣金接缝时,格罗夫斯想起妻子分娩前紧绷的肚皮——只不过这个金属胎儿包裹着64面体透镜,腹腔里填满了代号“瘦子“的钚-239球芯——总重量只有3400千克,却蕴含着毁天灭地的能量。
“将军,气象组第三次预警。“传令兵的声音在防空洞里激起回声,文件夹里的积雨云雷达图簌簌发抖,“西南方对流层出现切变,是否推迟引爆?“
格罗夫斯用雪茄点燃下一份报告,火苗顺着铀浓缩厂的电力预算窜到指尖。
“按原计划执行。”
观测站突然陷入死寂。二十码外的钚冶金专家停止擦拭金相显微镜,负责起爆电路的陆军上尉松开扳手,所有人都听见格罗夫斯将军咬碎雪茄过滤嘴的脆响。
青铜装置的第37号透镜反射着晨光,在沙漠上投下匕首状的阴影。铁塔顶端传来钢索绞盘转动的呻吟,倒悬的金属球体开始顺时针旋转,抛光表面将朝阳折射成支离破碎的光刃。
“三分钟倒计时!“
扩音器突然爆发的电流杂音惊飞了红尾鵟,也抖落了所有人眼睫睫毛上的冰晶。来自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的化学家们开始往铅桶里藏未开封的波旁酒,这是他们与陆军工程兵心照不宣的赌约——如果核裂变失败,这些酒将成为庆功宴的祭品。
“上帝该后悔把这片荒漠造得如此平坦。“后勤补给官班布里奇的声音在零下三摄氏度的空气中凝成白雾,他正在检查引爆装置的铂金触点,“我们就像在上帝的眼皮底下布置谋杀现场。“
“一分钟倒计时!“
恩利克·费米突然脱下羊毛背心裹住辐射计数器。这个动作让奥本海默想起芝加哥那个雪夜——当时费米也是这样用大衣保护仪表,仿佛那些钢铁仪器才是需要呵护的生命。
“恩利克,你妻子缝的护身符呢?“奥本海默注意到他空荡荡的领口。
“留在芝加哥大学的保险柜了。“费米将怀表贴在耳畔,“有些东西不该见证自己的造物主。“这时,伽马射线警报响起,费米赶忙摸出劳拉绣的丝绸手帕,开始记录中子通量数据。
十公里外的观测壕里,战地记者劳伦特·施罗德的莱卡相机镜头蒙上了防辐射铅玻璃,这个记录过诺曼底登陆的硬汉此刻正在手抖——胶片盒里的柯达胶卷将见证比一千个太阳更亮的光。
大地突然开始脉动。不是震动,而是某种原始的能量在玄武岩层下苏醒。
归零的时刻终于到来。
一道刺目的光芒划破了天际,仿佛太阳提前升起,将整个世界都笼罩在一片耀眼的白光之中。这不是白昼降临的明亮,而是所有物质在绝对光明中的消解。
费米用《晚邮报》碎片遮住眼睛,这是一个来自都灵的古老智慧:当无法承受光明时,就用文明的灰烬保护瞳孔。奥本海默却固执地睁大双眼,他必须记住每个纳秒的光谱变化——直到视网膜上烙满漂白世界的惨白。
在绝对寂静中诞生的光球,先是呈现出实验室里钚溶液特有的靛蓝色,继而转为芝加哥反应堆石墨块燃烧时的橙红,最后,又坍缩成《薄伽梵歌》描述的毗湿奴之瞳般的炽白。
方圆十公里的沙粒开始玻璃化,倒伏的约书亚树在强辐射中碳化成指向地狱的路标。
就像劳伦特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的那样——这一刻,上帝突然掀开了世界的底片。
奥本海默的呢喃被冲击波撕碎。他尝到口腔里的血腥味,不是来自爆轰波,而是自己咬破的舌尖——四年来他始终在模拟这个瞬间,却没人告诉他原爆闪光会让所有数学模型显得如此苍白。
......
当视网膜开始恢复功能时,周围的一切恍如地狱。
核爆产生的上千万度的高温和数百亿个大气压,使承载它的30米高铁塔彻底汽化,目前所及的范围内,沙石被熔化成了黄绿色的玻璃状物质。
随着爆炸的余波逐渐消散,一朵巨大的蘑菇云缓缓升起,如同地狱之门被缓缓打开,向世人展示着核力量的恐怖与壮丽。
它的形状诡异而美丽,却又让人心生敬畏,那是大自然与人类智慧交织出的最复杂、最矛盾的图景。
当蘑菇云开始呈现翡翠色的光晕时,奥本海默注意到一旁的技术顾问拉比在流泪。这个曾质疑链式反应道德性的年轻人,后来的核磁共振发明者,此刻正用希伯来语诵读《诗篇》第46篇——
“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看他使地怎样荒凉。他止息刀兵,直到地极。他折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
在爆心三公里处,劳伦特·施罗德的莱卡相机镜头正在熔化。这位曾记录过奥斯维辛焚尸炉的记者突然跪倒在地,超压冲击波掀翻了他的防辐射帐篷。
当柯达胶片在光辐射中自燃时,他疯狂地按动快门——这是人类第一次用影像记录自己文明的墓碑。
......
最新的数据传来,这次爆炸在沙漠表面凹陷成一个直径约500米的巨坑,而半径1600米的范围内,所有的动物全部死亡。
观测壕突然爆发的欢呼声让所有人怔住。劳伦特看到几个年轻技术员在跳踢踏舞,他们脚下的沙地还残留着伽马射线引发的荧光。
“成功了!成功了!“有人用德克萨斯口音反复嘶吼,这个曾在橡树岭监督铀分离的青年突然跪倒在地,抓起两把滚烫的沙子塞进口袋。
恩利克·费米跪在发烫的沙地上收集熔岩玻璃,掏出浸透汗水的丝绸手帕——上面的中子通量数据与三年前芝加哥实验的笔迹重叠。“误差率0.3%,“他露出试验成功后的第一个微笑,“比意大利面膨胀系数还精确。“
这时,冯·诺依曼举着算筹跑来,“两万吨当量,比当初预计的大20倍!“
“没错,”费米对着阳光举起一片紫色结晶:“看,多像但丁地狱第九层的颜色。“
当夕阳将蘑菇云染成血橙色时,奥本海默在吉普车后座找到了蜷缩的班布里奇。这位哈佛教授正用地质锤敲击一块完全玻璃化的玄武岩,叮当声里混杂着嘶哑的低语:
“我们打开了潘多拉之匣...却把希望锁在了里面,人类从此必须与自己的倒影共存。“
“是的,朋友,你说的没错,”奥本海默无限唏嘘道引用起印度圣典《薄伽梵歌》中的一句:“现在我成了死神,世界的毁灭者。”
1945年7月16日,当地时间5点29分21秒,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核爆产生的冲击波和电磁辐射,穿透天空射向无边的宇宙,并以光速向星际传播,人类文明正式进入核子时代。
......
沙粒在暮色中泛着幽蓝的荧光。奥本海默看着工兵用铅板包裹中子通量记录仪,那些精密齿轮与他的指纹一起被封存在防辐射箱里。
“恩里克,我已厌倦了制造武器,虽然它是正义的,想回去教书,你呢?”奥本海默率先开口道。
“听说了,芝加哥大学给你留了理论物理系主任的位置。“费米用镊子夹起片玻璃化的沙子,标本盒上的标签写着“三位一体石-001“,“但你的梵文课可能会吓跑研究生。“
奥本海默从大衣内袋掏出镀银酒壶,雪利酒在壶壁画出涟漪:“上周我重译了《奥义书》第三章——梵语里'裂变'与'轮回'是同源词。“他指向天际线残留的蘑菇云轮廓,“现在我知道为什么了。“
运输卡车的轰鸣惊散了食腐鸦群。格罗夫斯将军的指挥杖正敲打着钚运输箱,铅封上的鹰徽在夕阳中淌血般殷红。两名科学家不约而同背过身去——
那个装有“小男孩“铀芯的铅棺正在装车,它将在十七天后坠入广岛的晨雾。
他们知道,属于科学家的工作已经完成。接下来如何使用原子弹,则是政治家和军事家需要考虑的事情。
“我还没想好,你知道的,其实我的兴趣更多在天体物理和宇宙学。”费米想了想,继续说道:
“其实我最近在算银河系旋臂的星际尘埃分布。如果每个文明发展到能进行核聚变时必然自我毁灭,那么德雷克方程中的文明存续时间或许不会超过一万年。“
“我知道,你的费米悖论,现在已经人尽皆知。对了,你真相信有外星人?”奥本海默玩笑般问道。
“我不知道,我只是觉得宇宙那么大,如果只有我们,会不会太无趣了些?”费米也报以玩笑般回答。
“你说得对,对了,这封信送给你,算是一个纪念吧,希望我们还能再见。”奥本海默将一个信封递给了对方。
两位诺奖得主相顾一笑,然后握手告别。看着奥本海默的身影溶解在夕阳中,费米打开了信封,映入眼帘的是一封《致美国总统F.D.罗斯福的信》。
“总统先生:
最近的工作使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铀元素将成为一种新型的重要的能源。由此引起的许多问题需要我们提高警觉性,假如有必要的话,政府部门应当采取迅速的行动。因此我相信我有责任提醒您关注以下的事实和建议。
在过去的四个月里,通过约里奥在法国的工作,以及弗尔米和西拉德在美国进行的工作,使用大量的铀来建立核链式反应堆,从而产生巨大的能量和大量的新型类镭元素已成为可能。现在基本可以确定这将在不久的将来实现。
这种新的现象将引导着炸弹的构造,并且这是有可能的--尽管还不是那么确定--威力十分巨大的炸弹将因此而可能被制造出来。这样一颗单个的炸弹,用船运载,并在港口爆炸,将可能会摧毁整个港口以及周围的环境。然而,这样的炸弹对于空中运输可能显得太过于沉重。
美国只有很少量适合使用的铀矿石。有一些好的矿石在加拿大和捷克斯洛伐克,但最好的铀资源还是在刚果。
基于这样的情况你也许会认为在美国建造链式反应堆的物理学家和行政部门保持永久的关系是有必要的。对于你而言实现这样的可能的方式就是,将这一任务委托给一个你信任的人,而他将以一个非官方的身份进行工作。他的任务也许包括以下内容:
1.接近政府部门,熟悉未来的发展情况,并且给政府的工作提出建议,特别是关注为美国获取铀矿的供应。
2.通过提供资金加速实验活动,解决目前由预算有限的大学实验室来进行的问题。假如已经有资金,则通过和愿意为这一事业奉献的个人联系,或者是和具有必要设备的公司实验室进行合作。
我了解到德国实际上已经停止了捷克斯洛伐克矿山的铀交易,并对其进行了接管。它已经采取这样早的行动是可以理解的,根据德国副国务卿的儿子魏茨泽克,供职于柏林凯撒--威廉研究会,而在那里美国关于铀的活动一直在重复着。
综上,鉴于在不久的未来,人类必将探索使用原子能内部的庞大力量,我建议美国在这方面也必须高度重视,同时,我坚信,随着核子时代的到来,人类文明必将迈入一个崭新的阶段,或许,星辰大海对人类来说不再遥不可及!
你真诚的,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