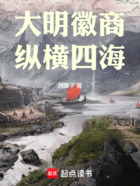
第24章 养兵先养粮
待一众伐木工大声感谢过后,江河向江大中问道:“江管事,你平日常在田庄上行走,不知道可有听说过咱们这边有人种植从外邦外来的甘薯与番麦吗?嗯,还有一种叫土豆的?”
他其实还是更习惯叫红薯和玉米,但他要说这两个名字,江大中就更不可能知道了。
眼下红薯的叫法确实是叫甘薯,因为他知道徐光启曾上过一道叫《甘薯疏》的奏章,好让朝廷能大力推广红薯的种植。可惜直到明朝灭亡,也没引起重视。
红薯原产于南美洲,大航海时期,西班牙人殖民南美,也得到了红薯这种新型农作物。后来西班牙人又殖民菲律宾,也把红薯带到了菲律宾,并成功种植。
菲律宾在此时名叫吕宋,万历年间,有一名福建人渡海到吕宋做生意,在发现红薯这种新作物后,回航时私藏了红薯苗带回福建,然后在家乡成功种植。
据说同时期,还有广东与云南这两条路线也有分别传入。但此时虽然传入了进来,却也都只是各地有小范围种植,还没有大面积推广普及开来,所以徐光启在民间发现这一高产作物后,便上疏朝廷,希望能由朝廷以政令的形式,在各地大量推广种值,解决粮食危机。
此时的玉米,也是同时存在有从海路与陆路传来的说法。海路便仍是西班牙在吕宋的殖民地,陆路则说是从西域那边一路传来。
而玉米最初的叫法就是番麦,也有叫西天麦的。至于土豆,江河倒是不知道最早的叫法,便干脆按自己前世习惯叫土豆了。
这三种高产的作物,其实都是原产于南美洲,最先的传播途径,也都跟西班牙这个殖民者有关。
江河当然没忘了明末还正好撞上了小冰河时期,各地天灾频发,粮食欠收。明朝的灭亡,也跟这一点大有关系。
所以这几样高产作物此时既然已经分别传入了进来,那他自然要弄到手,然后想办法大力推广种植。乱世除了要有兵,更要有粮。
所谓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如果连充足的粮食都没有,那也根本养不起兵,至少要让军队吃饱饭,才能谈得上有战斗力。
明朝后期军队拉胯,战力下滑,也跟这一点有极大关系。由于开中法的破坏,九边重镇经常缺粮,边军连饭都吃不饱,自然也就谈不上还有什么战斗力。
所以有句话叫,“明军不满饷,满饷不可敌”。如果能让明军满饷吃饱饭,那战斗力就有质的提升。
其实明末边军的家丁制度,也是缘于在朝廷长期军饷不足的情况下,将领们所做出的一种应对举措。
既然全军的军饷都已经欠了,无法满足所有士兵,那就不如接着欠,他们则集中资源养精锐,提高其中的的一部分战斗力。至于下面的普通士卒是逃走还是兵变,将领们既无能为力,也无所谓了。
反正只要优先保证他们家丁私兵的供养,真发生了闹饷的兵变,他们也能做到及时弹压。
“甘薯?番麦?土豆?”江大中闻言重复着念了一遍,有些茫然地向江河苦笑摇头道,“二公子,这几样东西的名字我都还是第一次听说呢,是真没见过,也不知到底有没有人种?”
“那你回头帮我去四处问问,打探打探,看有没有人种,如果有,立即向我来报。”江河闻言虽然有些失望,但这种情况本也就在他预料之中,眼下这几样东西都还没大规模普及开来。
红薯他倒是能够大致确定,这个时候福建、广东一带肯定有种。但限于这时代的交通条件,以及大社会环境下民间百姓对新事物的接受程度,尽管徽州也属于南方,离福建、广东两地并不算远,却也是还没能传过来。
不过传不过来,他回头也可以托人去那边打探,务必把种子与苗木带回来。
玉米也顺带到福建那边打探一番,西北的话就只能去甘肃那边打探了。至于土豆,他却是完全不知早期的种植信息,甚至也不确定土豆在这个时期传过来了没有。
毕竟对于土豆传入华夏的说法不一,有的说是明朝万历年间就传进来了,还有的则说要到十九世纪才能传进来,所以只能让人先四下打探去问一问了。
他眼下唯二能肯定的,就只有红薯与玉米,因为这两样东西后来在徐光启著作的《农政全书》里都有记载。
“是,二公子,我记下了,回头就帮你去四下问问。”江大中闻言,连忙答应道。
“有劳了!”江河笑着表达感谢。
“不敢当,不敢当!”江大中有些慌乱地摇手道,“为二公子你做事,那是应当的。”
江河笑了笑,道:“行了,那你去忙吧!”
江大中闻言又向江河拱手一礼,这才告辞离去。
那边书砚去了约有一顿饭功夫后,便见这小子当前领路而行,后面则有人推了辆双轮的平板布,车上装了满满几大坛酒。
因为自黄山南麓流出山中的几条溪流会汇入青弋江,并且最后一路连通至长江,所以距此下游不远处,便有一座乘船的码头。
这边砍倒的树木推落水中后,也是在漂流至码头处后重新收集整理,捆绑扎缚起来,然后再由拖船拖着一路运往下游。
黄山所流出的这几条溪流别看只是称溪,汇合在一起后也是称作香溪,包括青戈江的上流一段也称作泾溪,但实际上水流都并不小,河面也颇为宽阔。
称溪只是这边对水流的叫法,可并不是那种一步就能跨过去的山间小溪。比如绕歙县城而过的新安江支流练江,时下也是被叫练溪,但练溪的水流可是比香溪更大。
那边既有码头,经常有人来此乘船,便也逐渐发展成了一座颇为热闹的集镇,因为位于香溪畔,便被叫做香溪镇,临江的码头也叫香溪码头,并渐渐有了客栈、食肆等生意。
江河之前进山时吃的午饭,便是在那座香溪镇里吃的,而且镇上也有江家的生意与据点。
毕竟这个香溪码头也是江家木材生意链上的一个重要节点,所以那里却是有座木料场。
木材砍伐后,会在漂流到这里汇集整理,然后再用船拖运地沿江运输下去。但还有一部分,也有就地消化,就在徽州府本地售卖。
这部分本地售卖的,就会打捞起来,在那座木料场里晾晒去皮,还会做些粗略的分割。有的锯段,有的锯板。
分割开来的,多是打造家俱之用,整根的则一般用作建造房屋的梁柱,毕竟本地也是需要建房打家俱的。
见到书砚买了酒回来,众伐木工们立即大声欢呼,兴高采烈地过去帮忙卸酒。
明朝时期,虽然早已出现了高度数的蒸馏酒,但还没有完全普及开来,眼下也是北方比较流行,南方还是更喜欢喝传统的黄酒。徽州也是南方,所以此时书砚买来的这些便都是黄酒。
这些伐木工们前来干活,也都各自带了盛水的器具,大部分是更加易制的竹筒或葫芦之类。如江河与王微所用的水囊,需要用皮革来缝制,已经属于是高端货。
当下这些伐木工便各用带来的竹筒去盛酒,里面原本的水自然是倒了。至于没竹筒的也很好办,附近便生长有竹子,直接砍一根,就地取材便能制作。
所有伐木工在盛了酒后,都先一起举杯向江河敬酒,再度表对二公子的感谢。江河便也让人给他做了个竹杯,盛了杯酒,与众人共饮了一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