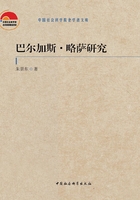
一 巴尔加斯·略萨的似水流年
家世与童年
巴尔加斯·略萨在他的长篇回忆录《水中鱼》中追忆了他大半生的经历。关于他的家世和童年,他是这样记述的:“我母亲19岁,她陪伴我外祖母卡门——她是塔克纳人——去塔克纳城。她们从阿雷基帕出发(当时全家住在这座城市里),去参加某位亲戚的婚礼,那是在1934年3月10日,就在省里那个小城市刚刚修建的、勉强维持的机场上,有人把帕那格拉电台(最早名叫泛美电台)的代理人埃内斯托·J.巴尔加斯介绍给她。此人29岁,是个很帅的小伙儿。我母亲迷上了他,那时起直到永远。他应该也爱上了她,因为她在塔克纳度过了几个星期的假期回到阿雷基帕后,他给她写了好几封信,甚至在帕那格拉电台搬到厄瓜多尔的时候,他还特地去跟她告别。就是在那次阿雷基帕的短暂逗留中,两个人正式确定了恋爱关系。后来的交往是通过书信进行的。直到一年后两人才重新见面,因为我父亲——帕那格拉电台又刚刚搬迁,这一次是迁往利马——又来到阿雷基帕,是来结婚的。1835年6月4日,二人结了婚,住在帕拉大街外祖父母家里,为此那所房子被精心地布置了一番。从保存下来的照片上(许多年后他们才拿给我看)可以看到多丽塔[1]穿着白色拖地半透明的薄纱长礼服,表情毫无光彩,反倒很严肃,她那一对深色的大眼睛里闪现着一片对难料的未来的询问的阴影。”[2]
“未来给的回答是一场灾难,婚礼后,他们立即去了利马,那时我父亲在帕那格拉电台任技师。他们住在米拉弗洛雷斯区阿尔半索·乌加特街的一幢小房子。从第一刻起,他就表露出略萨家族委婉的说法:‘埃内斯托的脾气很坏’。多丽塔被迫服从一种监狱的制度,禁止她去看朋友,尤其不准她去探索,必须永远呆在家里。只有在我父亲的陪伴下才能出门,或者去看电影,或者去拜访大舅子塞萨尔及其妻子奥里埃丽,他们也住在米拉弗洛雷斯区。吃醋的场面不断发生,无论什么借口,有时没有借口,并且可能引发暴力事件。”
“婚后不久,我母亲就怀孕了,等待我的出生。怀孕最初那几个月,她是一个人在利马度过的,偶尔有她嫂子奥里埃丽来做伴。我父母之间的家务争吵连续不断。对母亲来说,生活太困难了。尽管如此,她对我父亲的热烈的爱依然未减弱。有一天,外祖母卡门从阿雷基帕通知我母亲说,等我母亲分娩的时候她要来陪伴她。我父亲已经被派往拉帕斯去开设帕那塔拉的办公室。似乎这是世界上最自然的事:行前他对妻子说:‘你最好还是去阿雷基帕生孩子。’他就这样安排了一切,我母亲竟然没有怀疑他们策划的事情。1935年11月的一天早晨,他像一个亲密的丈夫那样告别了怀孕五个月的妻子。”
“此后他再也没有给她打电话,没有给她写信,也没有给她他还活着的任何信息,直到10年后,就是说,在不久前的那个下午,在波乌拉埃吉古伦防波堤上,我母亲对我透露说我一直以为在上天的那个父亲如今还在地上活着,并且到处游荡。”
“幸亏我外祖父母、我姨外婆艾尔维拉和她所有的兄弟姐妹表现得都很好。他们都爱她,保护她,使她感到虽然失去了丈夫,但她永远有一个家和一个家庭。”
“1936年3月28日黎明,经过长时间、痛苦的分娩后,我在帕拉大街一所住宅的二层楼上出生。外祖父通过帕那格拉电台给我父亲拍了一份电报,通知他我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他没有回报,我母亲给他写了一封信,告诉他已经给我取了马里奥这个名字,他也没有回信。”
不久后,塔内斯托和多拉通过一位亲戚和律师协议离婚。但是当10年后他们在皮乌拉和马里奥团聚时,马里奥的母亲仍然爱着塔内斯托。
“我出生后的第一年,我在出生的城市度过的唯一的一年,我一点也不记得的一年,对于我母亲、我外祖父母和其他家庭成员——按照保守派表达的全部含义,这是一个典型的阿雷基帕资产阶级家庭——是地狱般的一年,大家共同忍受着这个被遗弃的女儿、现在又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儿子的母亲的羞辱。对阿雷基帕那个具有偏见、又特别爱大惊小怪的社会来说,发生在多丽塔身上的秘密引起了许多流言蜚语。除了去教堂,我母亲绝对不上街,而专心照看这个新生儿。外祖母和姨外婆也帮助她,她们把这第一个外孙变成了家里最受溺爱的人儿。”
“我出生一年后,外祖父和萨伊德家族签订了一项耕种这个家庭在玻利维亚靠近圣克鲁斯的地方刚刚买下的几块地(赛皮纳庄园)的合同,他想在那里引种棉花,而他曾在卡马那成功种植过。尽管从来没有人对我讲过这件事,但是谁也不能从我头脑中除掉它:外祖父的大女儿的不幸遭遇——我母亲的被遗弃和离婚给大家带来的巨大烦恼,促使外祖父接受了那份使全家从阿雷基帕迁走的工作,此后他们再也没有回来。我母亲关于那次搬家曾这样说:‘搬到别的国家,别的城市去,在那里人们能让我安静地生活,这真叫我大大松了一口气。’”
“略萨一家搬到了科恰班巴,当时这座城市比圣克鲁斯那个小小的孤零零的小城更适合居住,安家之处是拉迪斯洛·卡夫列拉街的大房子。我在那里度过了我的全部童年,我记得那幢大宅子像一座伊甸园……”
“房子很大,我们都住在里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房间,外祖父母、姨外婆、妈妈和我、胡安舅舅、劳拉舅妈、他们的女儿南希和格拉迪兹、卢乔舅舅、豪尔赫舅舅和在智利学医的佩德罗舅舅,但是他经常回来和我们一起度假期。此外,还有女仆和厨娘,从来没少过3 人。在那个家里,我既自负又任性,甚至干出一些极端的事情,我简直成了一个小怪物。自负是因为对我外祖父母来说,我是第一个外孙;对舅舅们来说,我是第一个外甥;我还是可怜的多丽塔的儿子、一个没有了爸爸的孩子。没有爸爸,确切地说,我爸爸在天上,这并不是什么让我感到痛苦的事;恰恰相反,这个条件却为我提供了一种特权地位;缺少亲生父亲已经由几个代替者:外祖父和胡安、卢乔、豪尔赫与佩德罗舅舅,给了补偿。”我的顽皮行为导致我母亲在我5岁时就在拉萨勒学校给我报了名,这比修士们建议的早一年。不久我就在胡斯蒂尼亚诺修士的课上学会了阅读,这可是在埃吉古伦防波堤那个下午之前我的生活中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情;这多少平息了我的一些冲动。因为阅读“比利肯斯”、“佩内卡斯”和各种故事书与冒险图书变成了一件令人激动的事情,可以让我安静许多个钟头。不过阅读并不妨碍我游戏,我能把全班同学邀请到家里来喝茶,对这种过分的行为,外祖母和姨外婆——如果上帝和天堂存在的话,我希望她们能受到适当的奖励——只能一声不吭地忍受,还要卖力地为所有这些孩子做黄油面包、冷饮和牛奶咖啡。”
“直到1945年底以前我在玻利维亚期间,我一直相信圣婴的那些玩具,相信白鹳把娃娃从天上带到人间来,那些忏悔者所说的坏念头一个也没有从我的脑海里闪过。那些坏念头是后来出现的,那时我已经住在利马了。我是一个顽皮和爱哭的孩子,不过纯朴得像一朵百合花。在信仰上我是虔诚的。我记得第一次饮圣餐那一天,那是一个美丽的大事件;我记得拉萨勒学校的校长阿古斯丁修士每天下午在学校的小教堂里给我们上的那些预备课和那个激动人心的仪式——我穿着一身白衣服,全家人在场——我从科恰维巴大主教手里接过圣饼,这个显要的人物身披紫色的圣服,每当他从街上经过或者出现在拉迪斯拉奥·卡夫列拉(他曾任秘鲁驻玻利维亚领事,我外祖父也曾任秘鲁驻玻利维亚的名誉领事)的住宅里时,我总是赶紧上前去吻他的手。”
马里奥在科恰班巴拉萨勒学校读到小学4年级。“我记得《带面具的狐狸者》(每周讲三个故事的系列电影)中的‘影子’的冒险。这是那个时期的中心事件,当然也是阅读中的发现。”“对我来说,阅读成了一种令人着迷的经历。在每个圣诞节(这是一年中另一个美妙的时刻)前,我记得我总要请求圣婴给我带书来。我记得某年12月25日醒来时床铺周围都是书,那幅场景令人难忘。我的舅舅们都送书给我,特别是小说。有卡尔·麦[3],他是写遥远的西部故事的德国人,那个西部我从没有去过。然后是埃米利奥·萨尔加里[4],他写有《桑多甘》等小说。同样我也记得关于那个时期在全拉丁美洲流行的两个杂志的许多情况:一个是阿根廷的《比利肯斯》,一个是智利的《佩内卡》。这些杂志是为了读故事和连载小说;不是看国内的杂志。”(《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运动中的生命》,2003年,利马)
马里奥在皮乌拉的萨莱西亚诺学校读了小学五年级。在《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运动中的生命》[5]一书中,马里奥回忆说:“来到秘鲁,我感到非常兴奋,但这也是一件使我受到一定创伤的事情,因为在学校里我的说话方式受到了别人的嘲笑。我说话像个山区的人。就在那个时候我明白了婴儿的来历。我记得有一天我和阿塔迪兄弟、胖子西尔瓦,还有豪尔赫·萨尔一起在皮乌拉河里游泳,我听见他们谈论婴儿是怎样来到世界上的。我感到沮丧极了,因为我知道了男人和女人竟然干那么肮脏的事情。这使我受到了伤害。”
在这同一本书里,马里奥谈到了他这个读者的习惯:“在皮乌拉,我进行了大量的阅读。我是一个看书的疯子。我比在玻利维亚时读的书多得多。在拉莫斯·桑托拉亚的书店里,我是一个系统的购书人……我惊异地阅读描写吉列尔莫的系列小说,吉列尔莫是一个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孩子,他跟他的外祖父有着奇妙的关系,他跟外祖父一起玩各类顽皮的游戏……在皮乌拉,我开始写小诗……我妈妈给我很大鼓励,我的卢乔舅舅也写诗,年轻时就写,我是在他给我朗诵几首诗时知道的。我问他,诗是谁的。他没有说是谁的,所以我明白是他自己写的。”
1946年,多丽塔带着儿子马里奥去见他父亲。和父亲的相遇这件事彻底影响了这个孩子的命运,改变了他母亲、舅舅们和外祖父母对他的溺爱和娇惯。父亲的缺失和突然的相遇,深深地影响了这个作家,甚至也影响了他作品中的一些人物,《城市与狗》中的里奇,《酒吧长谈》中的昂布罗西奥和《玛伊塔的故事》中的玛伊塔,他们都有同样的矛盾。
马里奥和他的父母后来去了利马,在那里定居下来,但是新的冲突又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