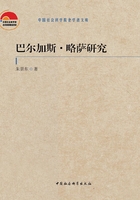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恩怨
巴尔加斯·略萨原本对加西亚·马尔克斯怀着深切的敬意,其间的友谊是深厚的。只因后来发生了一桩不愉快的事件,二人才断绝了来往,成了一对冤家。
早在巴尔加斯·略萨为自己的博士论文《加西亚·马尔克斯:一个弑神者的历史》写的序言中,他就毫无保留地表露对他那时所崇拜的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敬佩心情:“在他身上,有一个最让我欣赏和倾倒的特点,那就是他关于绘声绘色讲述趣闻轶事的本领。无论什么事情,一经他加工和编织,娓娓道来,便成了故事和趣闻。无论是政治的或是文学的见解,还是对人对事对国家的看法,抑或计划或抱负,他都能把它们变成轶事趣闻。他的聪明才智,他的文化修养,以及他的感觉反应,都有一种奇特罕见的、但又具有具体实在的印记……只要和这样的人交往,生活就会变成了飞流直下的轶事趣闻的瀑布。”此外,“他还是一个敢于极其大胆、极其自由地进行想象的人物。在他看来,夸张并非是一种扭曲现实的手段,而是审视现实的一种方式”。
在《致青年小说家》关于《风格》的信中,巴尔加斯·略萨称加西亚·马尔克斯为文学大师,说他的风格“与博尔赫斯不同,加西亚·马尔克斯不讲究朴实无华,而是追求丰富多彩,没有理想化的特色,而具有感官和快感的特点;他因为语言地道和纯正而属于古典传统,但是并不僵化,也不爱用古语,而是更乐于吸收民间成语、谚语和使用新词、外来词;他注重丰富的音乐感和思想的明快,拒绝复杂化或思想上的模棱两可。热情、有味道、充满音乐感、调动全部感官和身体的欲望,这一切都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风格中自然而然、毫不矫柔造作地表现出来;他自由地散发出想象的光辉,无拘无束地追求奇特的效果。当我们阅读《百年孤独》或《霍乱时期的爱情》时,一股强大的说服力压倒了我们:只有用这样的语言、这样的情绪和节奏讲述,里面的故事才令人感动;反之,如果抛开这样的语言,就不能像现在这样让我们着迷……继博尔赫斯之后,加西亚·马尔克斯成为西班牙语世界受模仿最多的作家;虽然有些弟子获得成功,就是拥有众多读者,但是不管他们多么善于学习,其作品都不如加西亚·马尔克斯那样具有鲜活的生命力……”[3]
自从1967年8月1日晚二人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西蒙·玻利瓦尔机场结为挚友之后,曾一起双双旅行,一起参加过千百次茶会,计划用两双手写小说,两个人一起谈论文学,书来信往,商谈一道书写关于1931年在两国发生的又悲又喜的战争的小说,两人决定一起描写一个没有载入史册的、似乎只有魔幻现实主义才会描写的事件。两个人计划各自花三年的时间以很少的费用住在巴黎拉克鲁瓦夫妇的旅馆里,旅馆的两位主人允许他们免费在他们的阁楼上住一个时期:加西亚·马尔克斯1957年住在那里,在那里构思了他的小说《没有人给写信的上校》,巴尔加斯·略萨则在1960年住在那里,写完了他的作品《城市与狗》。
与此同时,两个家庭的关系也十分密切,巴尔加斯·略萨甚至把加西亚·马尔克斯之子的名字贡萨洛取作自己的儿子的名字,彼此成了干亲。
在后来的日子里,巴尔加斯·略萨一直没有忘怀他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第一次相遇的情景。1967年8月1日晚上,为了去加拉加斯参加第13届拉丁美洲文学国际代表大会和首届罗慕洛·加列戈斯国际小说奖颁发仪式,巴尔加斯·略萨从伦敦乘飞机、加西亚·马尔克斯从墨西哥城乘飞机,两个人的飞机前后仅差几分钟在机场着陆。
巴尔加斯·略萨在三年后写的论文《加西亚·马尔克斯:一个弑神者的历史》中回忆说:“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我至今依然记得那天晚上他那副面容:由于刚下飞机(他对飞机总感到心头撞鹿般的害怕),仍感到有点惊慌,被摄影记者和文字记者包围追赶而显得局促不安。我们一见如故,成了好朋友。会议在加拉加斯开了两个星期,我们可以说是朝夕相处”,“他学着他的佩特拉姨妈的样子,板着脸儿,向读者们透露,他的小说都是他夫人写的,自己不过是署上个名字罢了,因为写得太糟糕了,而梅塞德斯又不愿意承担责任”。在这些玩笑背后,巴尔加斯·略萨断言,“有一个胆怯的人,对他来说,在扩音器前和面对公众讲话,简直是受罪”[4]。
无庸置疑,巴尔加斯·略萨和加西亚·马尔克斯之间的友谊是20世纪下半叶西班牙语世界两位文学大师之间最著名的友谊。但是到了8年后的1976年2月12日晚上,二人的友谊突然中断:那是在墨西哥城艺术剧院里,巴尔加斯·略萨狠狠一个耳光把加西亚·马尔克斯打倒,一只眼睛被打得青紫乌黑。当时放映的电影是雷内·卡尔多纳导演的《安第斯山的幸存者》。哥伦比亚文学批评家阿普莱约·门多萨认为被打断的是拉美文学界“最难忘最美丽的友谊”[5]。
那么,究竟是什么事导致巴尔加斯·略萨在墨西哥城影院里给加西亚·马尔克斯那记耳光呢?有两种说法,第一种是一种谣传,虽然来源不明,却广为流传:说加西亚·马尔克斯曾劝巴尔加斯·略萨的妻子帕特里西娅和她丈夫离婚,因为她丈夫对她不忠,或者帕特里西娅为报复她丈夫而对加西亚·马尔克斯说,他才是她所喜欢的伴侣。第二种说法来自一个有名有姓的人,他就是哥伦比亚作家胡安·戈萨因,那时他在巴兰基利亚《先驱报》工作,他说,面对巴尔加斯·略萨和他夫人所处的状况,加西亚·马尔克斯也许曾劝自己的妻子梅塞德斯去对帕特里西娅说,她应该和她丈夫分手。后来,这两种说法变成了一种:帕特里西娅和她丈夫和解,在某个时刻她对他讲了她跟“加沃”发生过的事情。
1976年2月12日那个傍晚发生的事情有目共睹:在墨西哥城那家影院里放映卡尔多纳的影片。池座里坐着拉丁美洲知识界的精英。电影演完了,灯亮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其夫人梅塞德斯陪同下向离他们几排远的朋友巴尔加斯·略萨走去,张开双臂想拥抱他一下,因为彼此已有好几个月未见面了。但是巴尔加斯·略萨却抡起右手给了他一记耳光,把他打倒在地。“这是对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巴塞罗那对帕特里西娅说的话的回答”,巴尔加斯·略萨如是说。
西班牙巴斯克人的后代、秘鲁记者佛朗西斯科·伊加图亚应邀来该影院看电影,但是他来晚了,看见加西亚·马尔克斯已经倒在地上。后来他在他的回忆录《流亡的痕迹》中记述了他亲眼目睹的情景:在电影院的门厅附近,有一群人,其中有女作家艾莱娜·波尼亚托夫斯卡,他们站在加西亚·马尔克斯周围。有人从一家肉铺弄来一块牛排,敷在加西亚·马尔克斯那只被打伤的右眼上,想为他消消肿。
在相距几米远的一家酒吧里,记者本哈明·旺格陪着沉默无言和像死人一样面孔苍白的巴尔加斯·略萨。人们在那里对伊加图亚讲述了刚刚发生的事情。后来伊加图亚把巴尔加斯·略萨送到了饭店,在房间里等着帕特里西娅。帕特里西娅来到后,毫不犹豫地责备了她丈夫,她说,他已经把她变成所有人的笑柄,“半个世界的人都管我叫加瓦[6]……”,她叫道,一面把桌上的一只大花瓶和几盏小灯朝无动于衷地呆在现场的巴尔加斯·略萨扔去。
好几家报纸刊登了这个事件。其中一家报纸甚至还刊登了一幅漫画,画着两个作家像两名拳击手在打斗。后来他们的政治态度的变化加大了两个人之间的裂痕:巴尔加斯·略萨走向自由主义,成为对卡斯特罗政权的愤怒批评者,加西亚·马尔克斯则成为依然支持古巴革命总司令卡斯特罗的少数知识分子之一。两个人谁也不肯谈论那一记耳光之前发生的事情。[7]但是当有人问他们之间已经破裂的友谊时,他们的脸上都会现出一丝怀念过去的情绪。这也许是因为那种关系对他们的生活十分重要,也许原因很简单:一提起两人的关系,二人都会怀恋那些逝去的年华。后来,出版社准备再版《加西亚·马尔克斯:一个弑神者的历史》,巴尔加斯·略萨表示同意,但不会删除最后一页上题为《坦言》的后记中的一句话:“如果没有许多朋友:梅塞德斯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帮助,我是不可能写出这篇论文的。”
但是直到加西亚·马尔克斯2014年4月逝世,这两位冤家也未能谋面握手言欢。但是巴尔加斯·略萨得知加西亚·马尔克斯过世的消息后,曾在秘鲁阿亚库乔市大街上对采访他的电视台记者表示:“一位伟大的作家走了,他的作品受到了广泛传播,为我们的语言文学带来了声誉。”然后又补充说:“他的小说将使他永存,将赢得任何地方的读者,他将依然活在大家记忆中。我向他的家庭表示哀悼。”此外,他还对记者说:“《百年孤独》我读过许多遍,因为我给学生们教过它,我多次上过关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课,最后一次是在普林斯顿大学……这是一本可以反复阅读的书,每次读都发现新东西。你不知道我是多么敬佩他,读这本书改变了我的人生……”这表明,巴尔加斯·略萨已摒弃前嫌,不再记恨他。
而加西亚·马尔克斯并非没有什么表示。在巴尔加斯·略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他通过特威特网给他发了一封祝贺信,信中说“你获了这个奖,我们拉平了。”巴尔加斯·略萨随后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对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于我获奖的祝贺,请你们替我向他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