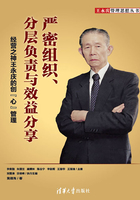
对关系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进一步讨论
“关系”和“结构”是台湾地区关系企业成长过程中的两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关键词。它们既总结了关系企业的特点,也概括了关系企业的特性。经由关系联结而成的结构,是关系企业的外在表现形式;经由结构划分而成的,用于规范各种关系的责权利原则,则是关系企业的内在运行机理。
历史事实表明,关系企业成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家是否能够及时根据关系来调整其结构,或是根据结构来理顺其关系。本书用“关系结构”这一复合概念来概括“关系”和“结构”之间的联系,亦即:关系是指人们为完成合作及交易所建立的一种结构化联系;而结构则是指人们赖以完成合作及交易的一张关系网络。其中,关系越强则结构越紧密,结构越紧密则关系又越强。
从表面上看,总管理处虽超然于各分子公司之上,但它至少表明各分子公司已经由总管理处联结为一个有机整体。事实上,总管理处就是各分子公司间相互联系的一个枢纽,或者说是一个中枢性内部控制机构更为妥当,只不过因为不同关系企业的发展战略和成长方式不同,自然以总管理处为核心形成的“关系结构”也各不相同,其中有的紧密,有的松散。
一般来说,“关系结构”越紧密,总管理处的控制性就越强,各分子企业对于总部组织的依赖性大于其独立性;反之“关系结构”越松散,总管理处的控制性就越弱,各分子企业对于总部的独立性大于其依赖性。在后一种情况下,总管理处在本质上也就非常类似于一个会员数量有严格限制,但却无强制性纪律约束的“商业俱乐部”。
在过去的十年中,“对于东亚经济奇迹的研究表明,缺乏对经济伦理与文化维度的研究,就不能很好地理解其经济增长和企业组织的逻辑” 。同样,如果说台湾是东亚经济奇迹的集中代表之一,那么对关系企业中“关系结构”的理论研究就应该从探讨其经济伦理与企业文化入手。
。同样,如果说台湾是东亚经济奇迹的集中代表之一,那么对关系企业中“关系结构”的理论研究就应该从探讨其经济伦理与企业文化入手。
早期的那批关系企业的创始人,他们遵循民族文化中的一些经济伦理创立企业,并把一些基本的,朴素的道德选择当作关系企业组织生存的逻辑。调查表明,诸如“勤劳朴实”、“诚实守信”等一类伦理规范,的确被这些创始人当作是调节其“关系结构”时所做出的道德选择。事实证明,恪守这些道德选择对于企业组织成长至关重要。
在对上百位关系企业创办人及其高级管理人员的访谈中,本书作者发现,建立情感和利益联系的伦理基础是信任。在公司治理的层面上,信任主要指“按规矩办事”,亦即“恪守道德选择”,大多数关系企业均接受“在各分子企业间,以及各关系企业与外界之间的拓展性交易中,的确存在着较高的信任度”这一观点。受访者普遍认为,建立上述信任基础意味着关系企业针对各分子公司及其与外界之间的交往与交易建立了某种特定的治理机制。
也就是说,在关系企业架构下,各分子企业间既要保持情感联系,同时更要“恪守道德选择”,因为各关系企业间越是相互信任,人们从更高频率、更多数量以及更有效率的交往与交易中获取的好处就越大;反过来说,好处越大,人们也就越是愿意按“关系规则”办事。在今天看来,这一点已几乎成了关系企业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连锁”效应。它意味着在关系一定的前提下,评价一家关系企业结构稳定性的指标可能就要看其是否建立了清晰的、且用于约束各种关系的“算账原则”。
更深层次的访谈结果表明,大多数关系企业已经或者正在经历着从“私人信任”到“社会信任”的演变。也可以这样下定义说,关系企业是人们为追求商业利润和情感联系而聚集在一起的一种特殊的企业组织形式。人们通过企业组织履行责任,行使权力并获取利益,如此交结而成的是一种“非个人化的,理性的信任治理结构” 。
。
这一点正是台湾走向工业社会,及其大部分工业企业由此实现集团化成长的一个重要伦理标志。换句话说,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台湾地区关系企业多是在家族企业的背景上成长起来的,但在岛内外新的政治与经济变革的双重作用下,早期的一些关系企业并没有完全选择“避免与那些跟自己没有私人关系的个人和企业进行交易”,而是“热衷于和非亲非故者建立私人关系网”,并因此而“显示出了高超的技巧” 。
。
幸运的是,一些关系企业虽特别注重人际关系网络,但却在做生意的过程中并没有过分依赖这一网络,从而使其节省了巨大的时间、精力和经济成本,并因为不缺少类似关系网而成功地与岛内外已有的企业展开竞争与合作。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关系企业倾向于将透过商业组织形成的情感联系比喻为“兄弟关系”,因为如此比喻不仅是为了寻求并保持彼此都需要的“家庭式忠诚”,同时更重要的是强调双方在交易与交往等合作中应自动具有善尽各自责任、权力和义务的自觉性。
本书作者的调查还发现,仅仅有“家庭式忠诚”还不够,因为在经济利益的诱惑或者成长过程中遇到的危机面前,这种“忠诚”根本就显得不堪一击,不论其原有关系网络的结构是否具有血缘联系。如果据此推测王永庆的动机,那么他设计关系企业公司治理结构的目的,就是希望“兄弟关系能成为主导企业价值创造活动的主体,而不仅仅是为了维持一个关系网络”。
岛内官产学界至今仍沿用欧美企业“两权分离”的经营模式来分析关系企业,有人甚至还把“核心关系圈既是所有者又是经营者”这一现象,简单地归结为是关系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不健全,以及是难以实现永续经营的根源等。但今天看来,这一观点并没有反映出关系企业演变的真实情况。事实是,从其诞生的那一刻起,关系企业就是台湾地区政治、经济与文化综合作用的产物。企业家完全是在当时当地的社会背景下,按照企业的现实需要,编织出了自己的“关系”与“结构”。
他们当中的一些有远见的企业家在企业初创时期,就已经意识到了家族制企业存在的各种弊端,并尝试用各种方法来调整企业的发展战略与结构,通过引入外部力量或关系 ,比如外部投资者和职业经理人等,以便能在核心关系圈内保持权力平衡,并维持其经营活力。“实际上,家族制在扩展中的成功,主要依赖于家族间的广泛结盟;而这早已超出了血缘和地缘划定的范围”
,比如外部投资者和职业经理人等,以便能在核心关系圈内保持权力平衡,并维持其经营活力。“实际上,家族制在扩展中的成功,主要依赖于家族间的广泛结盟;而这早已超出了血缘和地缘划定的范围” 。
。
但鉴于台湾经济社会的演进水平以及企业的实际情况,引入外部力量和关系非常困难,至少在短期内是如此,因为外部力量和关系的进入意向,虽说与企业的获利能力成正相关,但在某些情况下却与企业家的个人考虑和战略思路负相关。这一点也许是关系企业“两权分离”的进程显得非常缓慢的主要原因。或者说,主导关系企业发展的核心关系圈,可能根本就没有像美国企业那样,试图在一开始就愿意把所有权与经营权彻底分开。
在企业经营初期或陷入低谷的情况下,外部力量或关系进入的意愿最低。比如,王永庆在1956年前后就持有台塑公司约70%的股权,如此高比例持股并不是他本人刻意所为,而是台塑公司在当时因为原料卖不出去而陷入绝境,使得其他几位股东认为前途无望而萌生退意,于是为了维持多年的和谐关系,王永庆迫不得已只好割让板桥、松山两座砖厂及十多甲土地和他们交换台塑公司的股份,然后大家圆满分手。几十年后,王永庆在回忆这一段往事时说:“为了企业能生存下去,我当时也想出售自己的股份,但是谁要?”
这些史实说明,企业家并不一定是“去家族化”的主要阻力。他们在复杂的经营过程中,只是巧妙地采取了一些顺势而为的做法,不但就此成功保持住对企业的控制权,同时也因为亲自经营企业才使之度过重重危机。关系企业的治理经验证明,“两权分离”不一定是灵丹妙药;“两权不分离”也不一定能包治百病。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大背景下,关系企业能否实现永续经营的关键,主要还是看企业家能否在保持“兄弟关系”的同时,是否也能够同时建立起一套相应的“责权利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