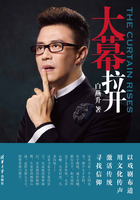
七岁红
童年留在我记忆里的也不都是贫穷落后的黯淡无光。童年是什么呢?40年前的一幕一幕清晰如昨。
童年是池塘边无尽的蛙鸣;
童年是枣树林痴迷的练声;
童年是邻家女清澈的眼睛;
童年是夜晚不停地数星星;
童年是田野里和太阳赛跑;
童年是帽子上的红五角星;
童年是唐诗三百首的懵懂;
童年是看倒影的那一口井。
……
除此之外,我的童年或许比周围的孩子们多了一份执着痴迷的乐趣,那就是对家乡戏河北梆子的喜爱。
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整个80年代,在京津冀,河北梆子很盛行。一有空儿,我便打开收音机聆听慷慨悲歌。
从我记事儿起,似乎天然地习惯河北梆子的高亢激越。
各个时期的河北梆子名家甚多,比如响九霄、魏连升、侯俊山、何景山、小香水、金钢钻、银达子、贾桂兰、刘香玉、李桂云、韩俊卿、金宝环、宝珠钻、王伯华、王玉磬、张淑敏、张惠云、阎建国、巴玉岭、刘玉玲……在河北出生的京剧大家东光人荀慧生、高阳人盖叫天、南宫人尚小云等,早年都曾为梆子演员。
张淑敏,我的最爱。我一直认为,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培养起来的河北梆子的杰出代表,尽管她37岁在“十年浩劫”中英年早逝,尽管她只有20多年的艺术生涯,但她却坚实地筑就了河北梆子的一座高峰。
她有着一副高音清脆锐利、低音浑厚遒劲、中音圆润通透的极富感染力的好嗓子,只听声音就能看到鲜活人物。她先从李桂云学艺,后拜贾桂兰为师,既融会了李桂云的润腔,又掌握了贾桂兰激昂的“硬上弓”的梆子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高超的演唱风格。后来她又受教于梅兰芳、荀慧生、常香玉、袁雪芬等艺术家,加之勤奋刻苦和聪慧悟性,她集各家各派之长,取姊妹艺术精华,颇显时代精神气质,别开生面,独树新风。
她的《杜十娘》,被评论家誉为“精彩细腻,简直是一件成熟的艺术精品”,“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小的时候,我时常抱着收音机,沉醉在艺术家们声情并茂荡气回肠的世界里,或喜或悲或爱或恨,忘却了写作业,忘却了放羊,忘却了吃饭……
十来岁的时候,我彻底兴奋了一回,现在想起来还是激动。有一天,天津的河北梆子名家女老生王玉磬老师到我们村来演出,接待并照顾她起居的,是我的姐姐。我至今都后悔没能近水楼台和她说几句话,准确地说,当时真是不敢走近她,只能远远地看着。
看见从收音机里走出来的真人,我更加纳闷疑惑:偏矮偏瘦的个头儿,哪来的气贯长虹、穿透九霄、响遏行云的嘹亮嗓音?
20年后的1999年,我终于有了去天津采访她的机会,那天我同样很激动。记得王玉磬老师在她老伴的陪同下走进宾馆大堂,我像看见久违的亲人一样赶紧迎上去,王玉磬老师对我似乎也不陌生,一老一少一见如故,我跟她说起20年前的往事,她笑得开心极了。
采访非常顺利,我圆了20年的梦,喜不自禁;王玉磬老师也很满意,看得出,她很喜欢我。这就是缘分!
回到北京没几天,我收到一箱子音像制品,全是王老师的戏,她让老伴给我寄来的,里面还有她的一封信。我喜出望外,如获至宝,至今珍藏。
……
2007年1月20日王玉磬老师去世了,我很想去天津送她,但那几天一直在录像,没能成行,总觉得缺失了什么。
2008年,在第24个教师节到来之际,我特别策划制作了“追忆大师,赏析精华”系列访谈,其中就有“铿锵玉磬——王玉磬”专辑,献上了我及河北梆子戏迷的真挚怀念和深情追忆。
河北梆子伴随我走过了美好的童年、少年,印象最深的电影是1976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由河北省跃进河北梆子剧团演出的《宝莲灯》,是由齐花坦、裴艳玲、田春鸟、周春山等主演的。我拎着小马扎走街串村地也不知看了多少遍,那个时候除了觉得电影神奇,也感到了河北梆子的震撼和伟大,很长一段时间,它占据着我的精神生活,尽管同一时期也看了大量其他剧种的电影。
我长到十五六岁的时候,燕赵大地刮起了一阵河北梆子旋风——河北电台举办的京津冀鲁河北梆子“鸣凤奖”大赛,那是一场真正的河北梆子总动员,几乎所有的演员和戏迷都行动了起来。
1984年首届“鸣凤奖”,张惠云夺冠,戏剧家范钧宏称她的演唱是“正宗河北梆子”。1986年第二届“鸣凤奖”,刘玉玲获旦角第一名,确立了她的京梆子独当一面的地位。像后来的张秋玲、彭艳琴、陈春等都是在20多年前的“鸣凤奖”中脱颖而出的。
主持戏曲节目以来,自然接触了不少家乡戏演员,也做了不少节目,2009年8月11日播出了我主持的“京津冀河北梆子青年名家专场”,除了当红的女演员许荷英、陈春、王洪玲外,还有几位难得的男演员。河北梆子声腔男女同宫同调,对男演员的嗓子是个极大的挑战,幸好现在还有王英会、刘凤岭、邱瑞德、李斌等为数不多的“男高音”支撑。
严格说,父亲是我学戏的启蒙老师。从我记事起,就知道父亲能教戏、会唱戏,是十里八村有名的师傅。
在家里,父亲经常不由自主地哼唱,那高亢激昂的河北梆子深深感染着我。到了过年过节的时候,村里总要唱大戏,父亲既是师傅又是主演,还经常被请到别的乡村班社教戏唱戏。再加上村里的红白喜事,人家总少不了请父亲参谋张罗。于是,在我眼里,父亲是个能人。
耳濡目染,久而久之,我很快就掌握了河北梆子的发音吐字,并且,能有板有眼地唱上几段。
七岁那年冬天,刚上小学一年级的我放学后没有回家,直奔俱乐部而去。在我儿时的记忆里,为了春节的演出,每年冬天村里都要排戏。此时,俱乐部门外雪花飘飘寒气逼人,里面却是丝竹管弦暖意融融。我只能站在窗外,从窗户的缝隙窥探。因为父母几次警告,不让我学这玩意儿。也许就是一种逆反心理作怪,我真的喜欢上了河北梆子。靠这种“偷窥”,我学会了《南天门》,也学会了《辕门斩子》、《秦香莲》、《蝴蝶杯》,等等。
有一天,趁父亲不在,我溜了进去。或许是被父亲阻止压抑了太久,不知哪来的勇气,竟给其他教戏的师傅们唱了一段现代戏《渡口》:“手握船篙心思想,这个人有点不正常。”一句唱罢,四座惊叹!那以后的四五年,我学戏唱戏,父亲再也没说什么。他被俱乐部全体师徒说服了,大伙儿异口同声:小升这孩子太有天分了……
记忆中,我最初演的都是配角,什么《秦香莲》里的冬哥、春妹,《二堂舍子》里的沉香、秋儿之类的小角色。很快,我主演了《南天门》,这个戏不长,但唱做并重。我的搭档叫胡运德,他的戏也很棒。
我们俩经常唱开场,如果后面的戏里有儿童,我们再赶妆。渐渐地,我成了远近闻名的“童星”,方圆几十里小有名气。逢年过节的,不光在本村本乡唱,还经常被邀请到十几公里外的乡村去演出。那可能是我最早的“走穴演出”了!
小小年纪,不光有人请,管吃住行,还能为家里挣“工分儿”,年底统一换算成钱。我开心得不行。印象中,父母好像并不在意这些,他们还是希望我能好好学习,考大学。
就这样,又过了几年,我学会了好几出大戏,在十里八村的名气直逼父亲。有一天,县剧团的某副团长下乡挑选剧团少年班演员,来到我们俱乐部,看了我的演出,跟我父亲说,要带我走。
这件事,是我后来才听说的。当时父亲就回绝了人家,说什么也不让我唱戏。
我因此开始记恨父亲了。

来自旧的青春
1986年5月,黄骅中学五四诗歌朗诵会后师生合影。中间站立者是我,那个时候才17岁,又老又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