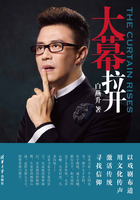
北漂时光
北京城的多余人
几经周折,河北台同意放人,但离当时国家广电部和国家人事部的调令下发日,已经过去半年多了。本来就对中央电视台敬畏有余亲切不足,加上拖延了这么长时间,面对即将开始的新工作新环境更加忐忑不安。
1994年的5月1日一早,我要离开河北向北京出发了。
我所在的“特别节目组”负责人杨建国(现为河北台副台长)早早来到电视台门口送我。我的同事李飞、王利民、狄晓伟、韩冀宏把行李装进面包车,他们要送我到北京,小许师傅驾车。
在河北台工作了不到三年。这三年给了我太多实践和锻炼,望着刚刚熟悉的广电厅大院,看着我曾经的办公小屋,心跌落到谷底,有一丝酸楚,那一刻没有了对北京的渴望。
人在回忆过往时,不管是高兴的还是苦涩的,不管是你主动选择的日子,还是不经意留下的痕迹,都会带上温情的色彩,更何况这里是我梦想开始的地方。
老主任印玉成拼命三郎般的老当益壮,资深摄像郗涛的侠气羁狂,编导张力辛温婉中透着霸气的才情,搭档王松梅多面娇娃般的美媚灵气,小乔和朱新豪爽与“闷骚”的颠倒绝配,陈彤笑佛般的宅心仁厚,焦树志貌似色情的绝对痴情,李光潜忍辱负重的沧桑青春,郑标满脸络腮的谨慎性情,刘丽萍工作生活两相宜的玲珑八面,司玉凯忧国忧民的悲情气质……忘不了这些曾经的良师益友,忘不了他们给我的激励和帮助!
飞扬的思绪被高速路上的一起严重车祸拽了回来。几辆车相撞,好几个人倒在血泊中,车上的我们面面相觑,心情沉重。
一路无话,只有汽车单调的声响。
来北京之前,就得知因报到太晚,中央台已没有了宿舍。我只好托朋友租下了电视台对过的“科情”地下室。尽管做了种种设想,也做了最坏打算,但现实远比想象的还要糟糕。“科情”的那间地下室在地下二层,不见一丝阳光,潮湿阴暗。六平米的小屋,除了单人床,其他空间放下我大包小包的行李,就再无立足之地了。见此情景,我没言语,李飞、王利民、狄晓伟、韩冀宏也没说话,但我知道那一刻,我们的心情是一样的。要知道,河北台给我这个单身汉破例分了一套当时省会最好的房子。
放下行李,在附近的“老来顺”,我请大家吃了顿涮羊肉,那顿饭我忘记了怎么吃完的,说了些什么也记不清了;总之,大家都把心情藏了起来,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儿,说着慰己慰人的话。
终于吃完了,他们送我回到楼门口,我让他们赶紧上了车,互道再见。车刚启动,那发动机的声音好像打开了我情感的闸门,我再也无法自制,泪水夺眶而出。看着他们走远了,我坐在旁边的花池沿儿上任泪水无声地流淌。
再见了,我的朋友;再见了,河北故乡!
那时,我想到了上大学临走前和父亲的那次分手。从此以后,我彻底离开了故乡,变成了游子。
离开河北台,同样需要勇气才能扯断和故乡相连的脐带。面对眼前的现实,已无法预知北京能否成为我的家,能否放飞我的梦想。想起生我养我爱我的故乡终于成了异乡,此刻,我不光没有了退路,也不知眼前的路该如何走。
有人说过: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
可我本来是有路走的,是自己不愿继续走,才落到今天无路可走的境地。
不知待了多久,才回到地下室。躺在床上,犹如笼中鸟思考着出路。
就是在那样痛苦无助郁闷难耐的日子里,我也天天给家乡的老父亲编织着美丽谎言,报喜不报忧。
记得有一天晚上,实在憋闷。天气闷,地下室也闷,我必须得出去走走,去哪儿?不知道。沿着小路往长安街方向走,几分钟就到了灯火辉煌的城乡贸易中心。1994年的初夏,公主坟立交桥刚刚动工。孤独地站在路灯下,看着进出商场的人们,看着工地上忙碌的工人,无所事事百无聊赖的我,像是这个城市里的多余人。
我漫无目的地顺着长安街辅路往东磨蹭着,什么都可以想,什么也都可以不想,看似悠闲自由,实则飘零落寞。长安街车水马龙的喧嚣似乎都被我的视听阻隔,我独自在自我的无极世界里游荡。不知何时下起了雨,没带雨具的我没有躲避,顺手摘下被雨水打得模糊不清的眼镜,好像早已准备等着淋雨似的,无知无觉,无爱无恨。
冒雨走了很久,突然面前一片开阔,原来到了天安门广场!这是我从小就向往的地方。此时,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好不容易来到了首都北京,可北京并没给我温暖,也没有我的向往和渴望。来京一个月,天天打水打饭,中午顺便在台里吃一份免费的盒饭,但吃得很不安,因为我无所作为,有种不劳而获占便宜的愧疚。我的存在也变得可有可无。这样的日子,这样的生活,决不是我想象的,更不是我想要的,可苦闷只能憋在心里默默承受。当时,按台里的规定,实习满三个月,且各方面反映良好才能办调动关系。且不说打水打饭是不是实习的重点,假如节目制片人说,我不胜任此栏目,我又该何去何从?
或许是到北京后的压抑积蓄得太久无处释放,走进神圣的天安门广场的那一刻,泪水伴着雨水倾泻而下。
没有了时间概念,我像个幽灵不知往何处飘荡。在广场周围转了好一会儿,觉得该往回走了。明天还得照例早到办公室,赶在大伙上班前,先收拾一下屋子卫生,之后打水,上午干些杂七杂八的活儿,再去提前排队打午饭。
雨还在下,从公主坟到天安门广场有多远,我至今没测量过。至少说,人在常态下,很少会徒步走个来回;但1994年初夏的那个夜晚,我用脚步丈量着我的隐忍和坚强。
沿着长安街往回走,望着道路两旁的万家灯火,酸涩的心绪涨满胸腔,北京这么大,竟没有我的容身之所!庆幸的是,当时我虽然有些悲观,但并没有讨厌北京这座城市;相反,我暗自发誓:既然选择了北京,就一定要留下来,混出个样儿,成为一个北京人,拥有自己的房子,自己的车!